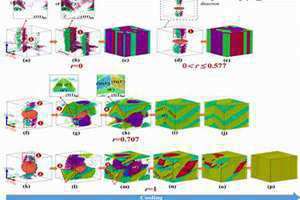
本文目录一览:
人在吃,秤在看!
渴望瘦成一道闪电,却总胖得一如既往。
连体重都控制不了,还怎么控制人生?
三句话,每一句都戳中了你的痛点?你也相信体重超标、身材不好,一定是因为自己又懒又馋?
NO!话说好身材,谁不爱?但发展成“身材焦虑”,那就该打住了。
每个人都渴望以良好的状态出现在他人面前,从外形到内心都获得他人的喜爱和欣赏,从而发展出积极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情感连接。因身材相貌不佳而被否定和拒绝,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情绪体验,会严重削弱个体的自尊和自我意识。
心理专家告诉你,适度进行体重和形象管理没什么问题,但因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而过分焦虑,则“伤心”又伤身。
年轻人的“流行病”
你也没能逃脱?
从“漫画A4腰”“反手摸肚脐”的身材PK,到对小码装的追捧,“瘦益求瘦”已经成为一种“流行病”。我们其实就处在一个“以瘦为美”的时代。很多人不管体重多少,总觉得自己要再瘦一点才好看。总是跟自己的身材“较劲”,这有意思吗?下面我们就来找一找心理的因。
1.有个消极意向的自我
如今,网络发达,社交媒介多样,互联网能随时随地将世界上好看的男性和女性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。面对大量优势形象的冲击,加上单一化的社会审美标准,人们很容易对自己的外形感到不满意,进而产生焦虑情绪,严重的甚至会发生体相障碍。体相障碍是指个体在客观上外貌正常,但主观上认为自己每个部位都丑陋无比,因而内心极其痛苦、焦虑的一种心理疾病。
2.过度关注自我形象
对自己的形象过度关注,对他人的评价过分在意。有一个比喻很形象,说的是这样的人就像生活在舞台的聚光灯下,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别人的关注和评论。因为在意,所以惶恐。但实际上,就算你做到了身材或颜值“无懈可击”,受到认可的并不是你的性格特质与思想内涵,那么,即便当下身材姣好,未来依旧有被挑刺的风险。
3.缺乏独立的自我
拥有独立的自我,是建立自信心的基础。对自己不认可,总想迎合别人,让别人喜欢和接纳自己,是导致“身材焦虑”的原因之一。关于社会舆论或环境舆论对身材的影响,你需要问清楚自己:对自我的不满意,究竟是因为无法取悦自己?还是因为无法取悦别人?如果是后者,那请你明白一点,不论你颜值多高、身材多好,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你。
别焦虑
其实你挺好看的!
美,是多样的。你,是唯一的。告别“身材焦虑”,我们一起从以下几方面入手。
1 树立正确的审美观
美是具有多样性的,不要被单一的审美观禁锢。“出厂设置”不同,外形、身材自然也不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和小缺陷,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的身材标准,能帮助你在社交中保持清醒,减少焦虑。
2 减少对身材的关注
身材好固然令人羡慕,但生活不应该被追求“好”身材填满。在日常生活中,试着主动关注你正在做或正在经历的每件事情,关注它们带给你的视觉、嗅觉、味觉、听觉和触觉感受,试着去体会那些你早已习以为常的细节。比如,吃东西的时候,你的舌头、牙齿和两颊是怎么互相配合完成咀嚼这个动作的?学会集中注意力,你将越来越擅长把注意力放到生活中其他重要的事情上去。
3 提升内在价值,增强自信
外貌美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自信,而自信却能让人更加美丽。多看书、多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,充实自己,提升自己的内在价值。优质的内心世界,会让人散发出自信的光芒。
4 适当运动,健康生活
研究表明,运动能让人分泌“快乐激素”多巴胺,从而减少焦虑。同时,以健康为前提进行运动,也是拥有好身材的有效方法。需要提醒的是,不少“身材焦虑症患者”,热衷于节食减肥,甚至通过催吐等极端方法,减少进食。这样的人很容易走上节食—厌食—拒食的道路,最终发展为厌食症。因“身材焦虑”走向疾病状态,甚至危及生命,那真是得不偿失。
有一句话说得好:
“身体只是承载你的精神容器,
尊重它,而不是和它较劲!”
作者|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
李则宣 黄任之
审核|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专家
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病学科主任
精神医学系主任 王小平
策划|谭嘉 余运西
编辑|梁婧
佛教中“体、相、用”的概念和思维方法,给我们认知事物提供了三个维度。 但是对于“体、相、用”的理解,因为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清晰的梳理,误解和误用甚多。比如南怀瑾就认为:
……拿中国唐代以后佛学原理来说,万物只有三个理则——体、相、用。如这茶杯,玻璃为“体”,“相”就是它的形状,“用”就是它的功用,即是可以盛液体的东西。抽象的思想,也是一样。譬如我们现在讲的,以孔子的《论语》思想为“体”,“相”就是二十篇《论语》,我们来研究、解释。“用”是了解孔子以后,才知反对孔子错在何处,又该怎样去弘扬中国文化,其“用”就在此……
——《论语别裁》
这段论述与亚里士多德“事物四因论(质料因、形式因、动力因和目的因)”非常接近,而且理解起来也不难。十八世纪中国学界倡导“西学为体,中学为用”,其中“体、用”的含义与南先生的理解是一致的。截至目前,对“体”的理解基本框定为“质地、材质”的意思。这样理解不能说不对,却是与佛教理论是不符的。那么到底什么是“体相用”呢?
我们先从最容易理解的“相”说起。
“相”即万物表现出來的现象,物理现象、化学现象、生理现象、心理现象……一句话,凡是用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“六根”能感触、意识到的,都是“相”。有人认为看得见、摸得着、听得见的才是“相”,其实不然,“相”也有看不见、摸不着、听不见的,比如电子波。有人认为物质范畴才是“相”,其实也不然,思想、精神范畴也是“相”,比如人们总结出来的所谓“规律”就是“相”,人们闭着眼睛做的白日梦也是“相”。显然,事物的材质、质地也能看得见、感知得到,也是“相”。所以,南怀瑾所说“玻璃是体”就与佛教的理论不符。
有了“相”就有了“用”。
不同的相,有不同的用。比如黏土做成碗(相) ,就有碗的功用;做成杯子(相) ,就有杯子的功用;做成佛像(相),就有教化的功用。同一个“相”,也可以有不同的“用”,比如杯子,可以用来装东西,也可用来变魔术。
佛教理论中为什么说“凡所有相,皆是虚妄”呢?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“用”随“相”变,“相”不是固定不变的,相的用也不是固定不度的,变才是“相”的绝对性。这与《易经》的“三易即变易、简易、不易”以及马哲理论的“世界是物质的,物质是运动和变化的”都是同一道理。《道德经》第2章讲道“有无相生,难易相成,长短相形,高下相盈,音声相和,前后相随,恒也”,这句话的含义就是“相的变化是永恒的”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,只有变化是不变的。“变化”可以作为判断事物“相”的绝对标准。
理解了“相”和“用”,我们再来说“体”。
佛教认为,万法之本“体”,即为万法之“性质”。所谓“性”,系以“无改”为义,是不生不灭,永远不变,系所谓“法尔如是”的。《道德经》中说的“人法地、地法天、天法道、道法自然”、“莫之命而常自然”、“辅万物之自然”……中的“自然”,和“法尔如是”类似,说的就是不以任何因素而改变。所以,“不变”可以作为判断事物“体”的绝对标准。这一点理解起来比较烧脑,我们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:
一、从“体”与“相”“用”三者的关系上来理解。上文我们说过,“体、相、用”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三个维度,“相”是事物中“变”的因素,那么“体”就应该是事物中“不变”的因素。事物中不变的因素有哪些呢?有很多!比如“变”就是事物中不变的因素,所以“变”算是“体”之其一;《道德经》中所说的“自然”,即“本来就那个样子”(上文中佛教所说的“法尔如是”),也是事物中恒常不变的因素,所以“自然”也算是“体”……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“体”是“本体、根本”的意思。《道德经》第16章说“夫物芸芸,各复归其根”,就是从“相”归到事物的“体”上。
二、从认知主体的认知方法上来理解。“相”是认知主体通过眼耳鼻舌身意等感觉器官来认知的,而“体”是认知主体通过“心”来“体会”的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“体”是“体会”的意思。
三、从“用”的角度来理解。上面说过,“体”有“体会”的意思,离不开“心”。如果我们的“心”是一面镜子的话,这面镜子是用来观照“相”的,有心还必须有“相”,才能有“用”;反过来,“相”必须通过“心”才能示其形、尽其用。如果没有“相”,心的镜子功用也就发挥不出来了。有“相”还要“心空”,如果“心”是满的、脏的、垢的,镜子的功用也发挥不出来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“体”和“心”是分不开的。佛教理论所说的“体”指的是“空”,即“缘起性空”中所说的那个“性空”,这个“空”还需要用“心”去体会。学习过佛理的人不难理解,但没有学习过佛理的人理解起来还是不太容易。在哲学上这叫“形而上”。我们再不妨拿大家耳熟能详的“看山三境界”来进一步说明。
第一重境界叫“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”。这一重境界相当于对“相”的认知,即用眼耳鼻舌身意等感觉器官和山这种事物进行的信息交流,我们用的手段是“看”,获得的信息是“相”。
第二重境界叫“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”。这一重境界就不是用“看(六根)”了,而是用我们的“心”去“观”。有人就问是不是闭上眼睛用心去臆想山水形象的信息呢?不是的!没有那么简单!用“心”去“观”,就是用“心”去“悟”。“观”什么?“悟”什么?悟山水的本体、本质、自然、恒、常、根……即《道德经》16章描述的“致虚极,守静笃。万物并作,吾以观复。夫物芸芸,各复归其根……”
我们用苏轼的《题西林壁》来说明:
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
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这一首诗说的就是第一重境界,这重境界得到的信息是“相”,从“相”上得到的信息就是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。如果闭上眼睛去回忆之前“看”到的庐山景象(相),我们就能“识得庐山真面目了吗”?还是不能。那么怎样才算“识得庐山真面目”呢?那就是用“心”去“观”,体悟到“庐山”这种事物的“根”。我们要“观”到那个“庐山真面目”,就要达到“看庐山不是庐山”的境界,那才是庐山的真面目。那么庐山的真面目是什么呢?是变,是空,是无,是我心,是自然……
“观”到庐山真面目之“体”后,“心”中无庐山之“相”,只有庐山之“性”,这就是“性空”。如果某时某刻你眼前出现了庐山的一幅照片、一幅画,或者听某人讲起庐山,你“心”中的“空”就会变成“有”,这就叫“真空妙有”。
有读者就要“大笑之”了:按照你的逻辑,任何事物,除了“相”和“用”不同,“体”不就一样了么?
还真是这样的,能参悟到万物一“体”,才算真正理解了“体”,万物一体即万物一理,你就对“体相用”理解透彻了。
所以,“观”的结果,我们的心就能体会到万物的“无”,这就是“涤除玄览”,这个时候,心就“空”了。
如果你还不理解,就记住一点:万物的“体”就是佛教所谓的“空”,《道德经》所谓的“无”。当然还有另外一些说法也是“体”的补充意思,比如:根、常、恒、自然等,都是从不同角度的不同表述。
悟透了万物一“体”,第三重境界“看山还是山,看水还是水”就达到了。没有第一重境界的“相”,你不知道万物有何用,这一重境界让你“知其然”;没有第二重境界的“体”,你不知道万物为何用,这一重境界让你“知其所以然”。“用”是连贯“相”和“体”的纽带。为什么最高的境界是“看山还是山,看水还是水”?因为你不仅看到了山水之“相”,也看到了山水之“体”,“相”和“体”相冲、相和,才有了山水之“用”。“有之以为利,无之以为用”——“相”就是“有”,“体”就是“无”。到了第三重境界,就能“识得庐山真面目”了,苏轼的诗就可以改成这样:
横观自然侧自然,远近高低各自然;
识得庐山真面目,只缘我心亦自然。
这就是“物我合一”的境界,即“得一”。
用“体相用”来认知事物,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。比如对“水”的认知,水有三态,三态又可因环境变化而千姿百态,这是其“相”、其“有”、其“实”;而其“体”、其“无”、其“空”,需要用“心”来参、悟,从而达到“用”。
明白了“体相用”的思维方法,就会“心无所住”。比如你“心”中有杯子的“体”,即使你看到一个从没见过的杯子,也能立即判断出它就是个杯子,从而拿来所用;遇到一件从未遇到的新生事物,也能从“心”中的“空”和“无”中找出认知和行动的对策,这就是《道德经》中“无为”的根本含义,即“从体而为”,而不是从“从相而为”。
我们拿“体相用”来理解《道德经》,也会变得更加简洁容易。
在《道德经》中,老子就是把“道”作为一件事物来描述的。第21章“道之为物,惟恍惟惚”,第25章“有物混成,先天地生”,明确指出“道”就是一物。既然是一物,就是“万物”之一,就如同“杯子”一样,也是可以用“体相用”三维分析法来进行认知的。
那么什么是“道”呢?这是至今仍争论不休的话题,其实参与争论者都是站在不同的维度来各说自话,意见当然不好统一。如果用“体相用”三维分析法,事情就变得简单了。因为“道”作为万物之一,只有从“体相用”再加上一个“名”,从这四个方面统筹兼顾,思考的结果才是全面的、系统的。我们不妨从这四个方面一一论述:
“道之名”——每个事物都有一个名字,那么“道”显然也是首先作为一个“名”来使用的。第1章“道可道、名可名”就有这层含义。第25章“有物混成,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,独立而不改,周行而不殆,可以为天地母。吾不知其名,强字之曰道,强为之名曰大”。这句话说得很明白,“道“和“大”同为一种“物”的名字。“道”和“大”的关系就相当于一个人有官名,同时还一个反映其生理特征的绰号,比如张三,也叫胖子。那么“道”是哪种“物”的名字呢?我认为,“道”就是“万物”的名字。人生活、生存于世,要与“万物”打交道,这个过程就是与“万物”进行能量、信息和价值交换的过程。具体到“万物”其中之一种,比如杯子、车子、房子等,很容易理解。但人类和个体,面对的不是一事一物、百事百物,而是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的事物。这所有的事物用文字表达出来就是“万物”,老子给“万物”起了个“名”就叫“道”。另外,“大”“天、地”“人”等有时也可以代指“道”,因为它们是“道”的有机组成部分或“道”的某些重要特征。
“道之相”——具体的万物都有各自特定的“相”,那么万物这个集合体“道”的“相”是什么呢?谁能把宇宙万物的“全息图像”描述出来呢?上文我们讲了,如果你白天看了庐山,晚上回到家闭着眼睛回忆一下脑子中的影像,虽然你用的是“心”,但“看(幻想)”到的仍然是“相”。那么要“看”到“万物的相”就更不容易了。那我们来看老子是怎样表述的吧——《道德经》第4章“道冲而用之”,第14章“视之不见”,第21章“孔德之容”,第25章“道之为物”,描写的就是万物即“道”的“相”。这些章节的共同特点是“虚幻”,所以给读者带来极大的困惑。但是,如果你明白“道”就是万物,你怎样来描述呢?你闭目冥想,把你见过的没见过的万物都在你的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切换,你要用文字描述出来,不正是老子笔下这些虚幻、缥缈、恍惚的文字吗?知道了这个原理,就会明白老子的文字功底是多么雄厚。而且老子怕大家不明白,又用了具体的事物作比喻,如婴儿、谷、溪、朴、水、曲等来描述“道之相”的某一特征,我们把这些都综合起来理解,“道之相”不就显得很立体了吗?
“道之体”——前边已经讲过,万物的“体”就是一、是根、是常、是恒、是自然……归根到底,就是佛教所说的“空”,也就是《道德经》所说的“无”。第14章描写的“其上不皦,其下不昧,绳绳兮不可名,复归于无物。是谓无状之状,无物之象,是谓惚恍”;第16章“夫物芸芸,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,静曰复命。复命曰常,知常曰明”;第48章“为学日益,为道日损。损之又损,以至于无为”;第49章“圣人常无心,以百姓心为心”,以及反复出现的“道常无名”“道常无为”……文中反复出现的不、无、静等,讲的就是“无”,就是“道之体”。
如果说“道之相”的获得途径是“为学日益”,那么“道之体”的获得途径就是“为道日损”,损到你的“心”是“无”的。当你“心是无的”即“无为”的时候,就达到“万物一体”的境界,你才能不“自是、自见、自矜、自伐”,才能像水一样无常形,才能如22章那样“曲则全”,才能像15章善为士者那样随事应变、微妙玄通,才能做到老子不厌其烦教导我们的怎样“善(擅长)”。
“道之用”——“道之用”就是对“道之体”和“道之相”的融合、运用。《道德经》第11章列举了车、器、室三个例子来说明“用”,得出“有之以为利,无之以为用”的结论。通过以上的分析,我们知道,万物之“相”就相当于万物的“有”,万物之“体”就相当于万物的“无”。在《道德经》中,“道之相”就是“有”,“道之体”就是“无”,对“道之体”和“道之相”的融合,就是“道之用”。那么对道又是如何用呢?老子也有不厌其烦的教导,比如:第1章“常无欲以观其妙;常有欲以观其徼”;第4章“道冲而用之或不盈”;第5章“多言数穷,不如守中”;“第28章的“三知三守”;第40章“反者道之动,弱者道之用”;第42章“万物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和”;第45章“大成若缺,其用不弊。大盈若冲,其用不穷”;第48章“为学日益,为道日损。损之又损,以至于无为”;第56章“塞其兑,闭其门;挫其锐,解其纷,和其光,同其尘”;第63章“为无为,事无事,味无味”;第71章“知不知,尚矣;不知知,病也”……讲的都是对“道之相”和“道之体”的“用”。
需要注意的是:在万物和道中,“相的有”和“体的无”是普遍性的,和《道德经》第11章所列举的三个例子的“有”“无”是不同的。第11章所举的三个例子中的“有”和“无”其实都属于“相”的范畴,因为车子、器物、房室等的“无”虽然看不见摸不着,但它是可感知可意识的。包括我们有的学习者喜欢用“看到半个西瓜”的例子来说明有和无的关系,这个例子中的有和无也是“相”。我在《道德经演义(15)》就有特别强调,老子通过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“有”和“无”是为了证明出“有之以为利,无之以为用”这个理论的,并非是“器物空间之无”就是“道之无”,这一点要特别注意。我看网上有很多人对“无”和“有”争论不休,其实没有真明白,脑子里还是糊涂的。“相的无”虽然看不见、摸不着,但它随“相的有”而变化,有变化就是“相”。“体”的“无 ”是恒定的,“体的无”才是“道的无”。
这一点确实不好理解,所谓“悟道”其实悟的就是这一点。简化一点,大家记住“无”就是“心无所住”就行了。【皂罗袍3】先生有一个“空车装货”的例子,比喻得很恰当。
通过以上论述,我们把“道”的“名”“相”“体”“用”综合在一起,很容易得出“道”的全息图象。如果你认真读了以上的文字,我相信能基本理解和明白《道德经》中大部分概念和表述。比如“大”,既是“道”的别称,又是“道之相”的重要特征。再如“自然”,讲的就是“道之体”的本性。再如“冲”和“中”,讲的就是对“道之体”和“道之相”的融合运用。再如“损”和“益”,“益”的是对“道之相”信息的积累,“损”的是对积累的“道之相”信息的辨伪存真。再如“反者道之动”,就是从“道之相”到“道之体”的感悟;“弱者道之用”就是从“道之体”到“道之相”及“道之用”的生发。再如“无心”,就是用“心”融入“道之体”的觉悟……顺着这个思路,你就可以将所有的概念从“名”“相”“体”“用”四个方面进行解构,肯定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“相体用”或者“名相体用”适用于万事万物,可以作为我们日常的思维方法。所以老子说“吾道甚易知甚易行”而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,多数人只是“看”到了“相”,而不会用“心”去观照“体”,不会从“体”或“万物一体”出发认知万物,不会“无为”,导致的结果是凡事考虑不到变化,思维形成定势,从而自是、自见、自矜、自伐。
有些人学佛学道或有所感悟后,倒是明白了“凡所有相皆是虚妄”的道理,也知道了“空”和“无”是怎么一回事,但又陷入另一个误区,即对“相”一概否定和排斥,只相信“心”中的那个“空”或者“无”。比如有名的“幡动心动”比喻,有人就只相信“心动”,不相信“幡动”。佛性真空,不是不显现,因为起用必显现。假如空了没有相,即不是自性了。因为有心必有相,心就是相,相就是心,心相不二。镜子里一定有影子,没有影子不成为镜子,因为没有妙用,佛性就变为死空、顽空。“真空”和“妙有”是一事两面,是“有之以为利,无之以为用”的关系。《道德经》的道理是一样的,讲“体之无”,必伴随着“相之有”。有无相冲、相中、相和、相融,万事万物才有其“用”。
通过以上的分析,大家是不是觉得“道”一点也不神秘,“道”就在我们身边,老子所说的“吾道甚易知甚易行”之言一点儿也不虚,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之言一点也不妄,庄子说的“道在屎溺”话糙理不糙。
用“体相用”来指导我们的生活也是非常简便可行的法则。比如:一个人生活生存于世,同时有多种身份角色,不同的身份角色就是一个人的“相”,不同的“相”有不同的“用”,怎样才能“用”得好,那就要“不住相”,你的心之“体”永远保持“空、无”的状态,当领导的时候好好当领导,不要把当父亲的角色运用到当领导上;当父亲的时候好好当父亲,不要把当领导的角色运用到当父亲上;面对不同的境遇,你始终保持空杯心态,这就是“冲而用之或不盈”“不欲盈”“蔽而新成”“不如守中”“外其身”“身下之”“为而不争”……这些教导的含义所在。
明白了这个道理,再来读第15章描述的“善为士者”,第27章描述的“五善”,第28章描述的能“知”会“守”……就豁然开朗了。
人在吃,秤在看!
渴望瘦成一道闪电,却总胖得一如既往。
连体重都控制不了,还怎么控制人生?
三句话,每一句都戳中了你的痛点?你也相信体重超标、身材不好,一定是因为自己又懒又馋?
NO!话说好身材,谁不爱?但发展成“身材焦虑”,那就该打住了。
每个人都渴望以良好的状态出现在他人面前,从外形到内心都获得他人的喜爱和欣赏,从而发展出积极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情感连接。因身材相貌不佳而被否定和拒绝,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情绪体验,会严重削弱个体的自尊和自我意识。
心理专家告诉你,适度进行体重和形象管理没什么问题,但因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而过分焦虑,则“伤心”又伤身。
年轻人的“流行病”
你也没能逃脱?
从“漫画A4腰”“反手摸肚脐”的身材PK,到对小码装的追捧,“瘦益求瘦”已经成为一种“流行病”。我们其实就处在一个“以瘦为美”的时代。很多人不管体重多少,总觉得自己要再瘦一点才好看。总是跟自己的身材“较劲”,这有意思吗?下面我们就来找一找心理的因。
1.有个消极意向的自我
如今,网络发达,社交媒介多样,互联网能随时随地将世界上好看的男性和女性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。面对大量优势形象的冲击,加上单一化的社会审美标准,人们很容易对自己的外形感到不满意,进而产生焦虑情绪,严重的甚至会发生体相障碍。体相障碍是指个体在客观上外貌正常,但主观上认为自己每个部位都丑陋无比,因而内心极其痛苦、焦虑的一种心理疾病。
2.过度关注自我形象
对自己的形象过度关注,对他人的评价过分在意。有一个比喻很形象,说的是这样的人就像生活在舞台的聚光灯下,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别人的关注和评论。因为在意,所以惶恐。但实际上,就算你做到了身材或颜值“无懈可击”,受到认可的并不是你的性格特质与思想内涵,那么,即便当下身材姣好,未来依旧有被挑刺的风险。
3.缺乏独立的自我
拥有独立的自我,是建立自信心的基础。对自己不认可,总想迎合别人,让别人喜欢和接纳自己,是导致“身材焦虑”的原因之一。关于社会舆论或环境舆论对身材的影响,你需要问清楚自己:对自我的不满意,究竟是因为无法取悦自己?还是因为无法取悦别人?如果是后者,那请你明白一点,不论你颜值多高、身材多好,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你。
别焦虑
其实你挺好看的!
美,是多样的。你,是唯一的。告别“身材焦虑”,我们一起从以下几方面入手。
1 树立正确的审美观
美是具有多样性的,不要被单一的审美观禁锢。“出厂设置”不同,外形、身材自然也不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和小缺陷,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的身材标准,能帮助你在社交中保持清醒,减少焦虑。
2 减少对身材的关注
身材好固然令人羡慕,但生活不应该被追求“好”身材填满。在日常生活中,试着主动关注你正在做或正在经历的每件事情,关注它们带给你的视觉、嗅觉、味觉、听觉和触觉感受,试着去体会那些你早已习以为常的细节。比如,吃东西的时候,你的舌头、牙齿和两颊是怎么互相配合完成咀嚼这个动作的?学会集中注意力,你将越来越擅长把注意力放到生活中其他重要的事情上去。
3 提升内在价值,增强自信
外貌美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自信,而自信却能让人更加美丽。多看书、多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,充实自己,提升自己的内在价值。优质的内心世界,会让人散发出自信的光芒。
4 适当运动,健康生活
研究表明,运动能让人分泌“快乐激素”多巴胺,从而减少焦虑。同时,以健康为前提进行运动,也是拥有好身材的有效方法。需要提醒的是,不少“身材焦虑症患者”,热衷于节食减肥,甚至通过催吐等极端方法,减少进食。这样的人很容易走上节食—厌食—拒食的道路,最终发展为厌食症。因“身材焦虑”走向疾病状态,甚至危及生命,那真是得不偿失。
有一句话说得好:
“身体只是承载你的精神容器,
尊重它,而不是和它较劲!”
作者|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
李则宣 黄任之
审核|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专家
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病学科主任
精神医学系主任 王小平
策划|谭嘉 余运西
编辑|梁婧
佛教中“体、相、用”的概念和思维方法,给我们认知事物提供了三个维度。 但是对于“体、相、用”的理解,因为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清晰的梳理,误解和误用甚多。比如南怀瑾就认为:
……拿中国唐代以后佛学原理来说,万物只有三个理则——体、相、用。如这茶杯,玻璃为“体”,“相”就是它的形状,“用”就是它的功用,即是可以盛液体的东西。抽象的思想,也是一样。譬如我们现在讲的,以孔子的《论语》思想为“体”,“相”就是二十篇《论语》,我们来研究、解释。“用”是了解孔子以后,才知反对孔子错在何处,又该怎样去弘扬中国文化,其“用”就在此……
——《论语别裁》
这段论述与亚里士多德“事物四因论(质料因、形式因、动力因和目的因)”非常接近,而且理解起来也不难。十八世纪中国学界倡导“西学为体,中学为用”,其中“体、用”的含义与南先生的理解是一致的。截至目前,对“体”的理解基本框定为“质地、材质”的意思。这样理解不能说不对,却是与佛教理论是不符的。那么到底什么是“体相用”呢?
我们先从最容易理解的“相”说起。
“相”即万物表现出來的现象,物理现象、化学现象、生理现象、心理现象……一句话,凡是用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“六根”能感触、意识到的,都是“相”。有人认为看得见、摸得着、听得见的才是“相”,其实不然,“相”也有看不见、摸不着、听不见的,比如电子波。有人认为物质范畴才是“相”,其实也不然,思想、精神范畴也是“相”,比如人们总结出来的所谓“规律”就是“相”,人们闭着眼睛做的白日梦也是“相”。显然,事物的材质、质地也能看得见、感知得到,也是“相”。所以,南怀瑾所说“玻璃是体”就与佛教的理论不符。
有了“相”就有了“用”。
不同的相,有不同的用。比如黏土做成碗(相) ,就有碗的功用;做成杯子(相) ,就有杯子的功用;做成佛像(相),就有教化的功用。同一个“相”,也可以有不同的“用”,比如杯子,可以用来装东西,也可用来变魔术。
佛教理论中为什么说“凡所有相,皆是虚妄”呢?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“用”随“相”变,“相”不是固定不变的,相的用也不是固定不度的,变才是“相”的绝对性。这与《易经》的“三易即变易、简易、不易”以及马哲理论的“世界是物质的,物质是运动和变化的”都是同一道理。《道德经》第2章讲道“有无相生,难易相成,长短相形,高下相盈,音声相和,前后相随,恒也”,这句话的含义就是“相的变化是永恒的”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,只有变化是不变的。“变化”可以作为判断事物“相”的绝对标准。
理解了“相”和“用”,我们再来说“体”。
佛教认为,万法之本“体”,即为万法之“性质”。所谓“性”,系以“无改”为义,是不生不灭,永远不变,系所谓“法尔如是”的。《道德经》中说的“人法地、地法天、天法道、道法自然”、“莫之命而常自然”、“辅万物之自然”……中的“自然”,和“法尔如是”类似,说的就是不以任何因素而改变。所以,“不变”可以作为判断事物“体”的绝对标准。这一点理解起来比较烧脑,我们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:
一、从“体”与“相”“用”三者的关系上来理解。上文我们说过,“体、相、用”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三个维度,“相”是事物中“变”的因素,那么“体”就应该是事物中“不变”的因素。事物中不变的因素有哪些呢?有很多!比如“变”就是事物中不变的因素,所以“变”算是“体”之其一;《道德经》中所说的“自然”,即“本来就那个样子”(上文中佛教所说的“法尔如是”),也是事物中恒常不变的因素,所以“自然”也算是“体”……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“体”是“本体、根本”的意思。《道德经》第16章说“夫物芸芸,各复归其根”,就是从“相”归到事物的“体”上。
二、从认知主体的认知方法上来理解。“相”是认知主体通过眼耳鼻舌身意等感觉器官来认知的,而“体”是认知主体通过“心”来“体会”的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“体”是“体会”的意思。
三、从“用”的角度来理解。上面说过,“体”有“体会”的意思,离不开“心”。如果我们的“心”是一面镜子的话,这面镜子是用来观照“相”的,有心还必须有“相”,才能有“用”;反过来,“相”必须通过“心”才能示其形、尽其用。如果没有“相”,心的镜子功用也就发挥不出来了。有“相”还要“心空”,如果“心”是满的、脏的、垢的,镜子的功用也发挥不出来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“体”和“心”是分不开的。佛教理论所说的“体”指的是“空”,即“缘起性空”中所说的那个“性空”,这个“空”还需要用“心”去体会。学习过佛理的人不难理解,但没有学习过佛理的人理解起来还是不太容易。在哲学上这叫“形而上”。我们再不妨拿大家耳熟能详的“看山三境界”来进一步说明。
第一重境界叫“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”。这一重境界相当于对“相”的认知,即用眼耳鼻舌身意等感觉器官和山这种事物进行的信息交流,我们用的手段是“看”,获得的信息是“相”。
第二重境界叫“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”。这一重境界就不是用“看(六根)”了,而是用我们的“心”去“观”。有人就问是不是闭上眼睛用心去臆想山水形象的信息呢?不是的!没有那么简单!用“心”去“观”,就是用“心”去“悟”。“观”什么?“悟”什么?悟山水的本体、本质、自然、恒、常、根……即《道德经》16章描述的“致虚极,守静笃。万物并作,吾以观复。夫物芸芸,各复归其根……”
我们用苏轼的《题西林壁》来说明:
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
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这一首诗说的就是第一重境界,这重境界得到的信息是“相”,从“相”上得到的信息就是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。如果闭上眼睛去回忆之前“看”到的庐山景象(相),我们就能“识得庐山真面目了吗”?还是不能。那么怎样才算“识得庐山真面目”呢?那就是用“心”去“观”,体悟到“庐山”这种事物的“根”。我们要“观”到那个“庐山真面目”,就要达到“看庐山不是庐山”的境界,那才是庐山的真面目。那么庐山的真面目是什么呢?是变,是空,是无,是我心,是自然……
“观”到庐山真面目之“体”后,“心”中无庐山之“相”,只有庐山之“性”,这就是“性空”。如果某时某刻你眼前出现了庐山的一幅照片、一幅画,或者听某人讲起庐山,你“心”中的“空”就会变成“有”,这就叫“真空妙有”。
有读者就要“大笑之”了:按照你的逻辑,任何事物,除了“相”和“用”不同,“体”不就一样了么?
还真是这样的,能参悟到万物一“体”,才算真正理解了“体”,万物一体即万物一理,你就对“体相用”理解透彻了。
所以,“观”的结果,我们的心就能体会到万物的“无”,这就是“涤除玄览”,这个时候,心就“空”了。
如果你还不理解,就记住一点:万物的“体”就是佛教所谓的“空”,《道德经》所谓的“无”。当然还有另外一些说法也是“体”的补充意思,比如:根、常、恒、自然等,都是从不同角度的不同表述。
悟透了万物一“体”,第三重境界“看山还是山,看水还是水”就达到了。没有第一重境界的“相”,你不知道万物有何用,这一重境界让你“知其然”;没有第二重境界的“体”,你不知道万物为何用,这一重境界让你“知其所以然”。“用”是连贯“相”和“体”的纽带。为什么最高的境界是“看山还是山,看水还是水”?因为你不仅看到了山水之“相”,也看到了山水之“体”,“相”和“体”相冲、相和,才有了山水之“用”。“有之以为利,无之以为用”——“相”就是“有”,“体”就是“无”。到了第三重境界,就能“识得庐山真面目”了,苏轼的诗就可以改成这样:
横观自然侧自然,远近高低各自然;
识得庐山真面目,只缘我心亦自然。
这就是“物我合一”的境界,即“得一”。
用“体相用”来认知事物,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。比如对“水”的认知,水有三态,三态又可因环境变化而千姿百态,这是其“相”、其“有”、其“实”;而其“体”、其“无”、其“空”,需要用“心”来参、悟,从而达到“用”。
明白了“体相用”的思维方法,就会“心无所住”。比如你“心”中有杯子的“体”,即使你看到一个从没见过的杯子,也能立即判断出它就是个杯子,从而拿来所用;遇到一件从未遇到的新生事物,也能从“心”中的“空”和“无”中找出认知和行动的对策,这就是《道德经》中“无为”的根本含义,即“从体而为”,而不是从“从相而为”。
我们拿“体相用”来理解《道德经》,也会变得更加简洁容易。
在《道德经》中,老子就是把“道”作为一件事物来描述的。第21章“道之为物,惟恍惟惚”,第25章“有物混成,先天地生”,明确指出“道”就是一物。既然是一物,就是“万物”之一,就如同“杯子”一样,也是可以用“体相用”三维分析法来进行认知的。
那么什么是“道”呢?这是至今仍争论不休的话题,其实参与争论者都是站在不同的维度来各说自话,意见当然不好统一。如果用“体相用”三维分析法,事情就变得简单了。因为“道”作为万物之一,只有从“体相用”再加上一个“名”,从这四个方面统筹兼顾,思考的结果才是全面的、系统的。我们不妨从这四个方面一一论述:
“道之名”——每个事物都有一个名字,那么“道”显然也是首先作为一个“名”来使用的。第1章“道可道、名可名”就有这层含义。第25章“有物混成,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,独立而不改,周行而不殆,可以为天地母。吾不知其名,强字之曰道,强为之名曰大”。这句话说得很明白,“道“和“大”同为一种“物”的名字。“道”和“大”的关系就相当于一个人有官名,同时还一个反映其生理特征的绰号,比如张三,也叫胖子。那么“道”是哪种“物”的名字呢?我认为,“道”就是“万物”的名字。人生活、生存于世,要与“万物”打交道,这个过程就是与“万物”进行能量、信息和价值交换的过程。具体到“万物”其中之一种,比如杯子、车子、房子等,很容易理解。但人类和个体,面对的不是一事一物、百事百物,而是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的事物。这所有的事物用文字表达出来就是“万物”,老子给“万物”起了个“名”就叫“道”。另外,“大”“天、地”“人”等有时也可以代指“道”,因为它们是“道”的有机组成部分或“道”的某些重要特征。
“道之相”——具体的万物都有各自特定的“相”,那么万物这个集合体“道”的“相”是什么呢?谁能把宇宙万物的“全息图像”描述出来呢?上文我们讲了,如果你白天看了庐山,晚上回到家闭着眼睛回忆一下脑子中的影像,虽然你用的是“心”,但“看(幻想)”到的仍然是“相”。那么要“看”到“万物的相”就更不容易了。那我们来看老子是怎样表述的吧——《道德经》第4章“道冲而用之”,第14章“视之不见”,第21章“孔德之容”,第25章“道之为物”,描写的就是万物即“道”的“相”。这些章节的共同特点是“虚幻”,所以给读者带来极大的困惑。但是,如果你明白“道”就是万物,你怎样来描述呢?你闭目冥想,把你见过的没见过的万物都在你的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切换,你要用文字描述出来,不正是老子笔下这些虚幻、缥缈、恍惚的文字吗?知道了这个原理,就会明白老子的文字功底是多么雄厚。而且老子怕大家不明白,又用了具体的事物作比喻,如婴儿、谷、溪、朴、水、曲等来描述“道之相”的某一特征,我们把这些都综合起来理解,“道之相”不就显得很立体了吗?
“道之体”——前边已经讲过,万物的“体”就是一、是根、是常、是恒、是自然……归根到底,就是佛教所说的“空”,也就是《道德经》所说的“无”。第14章描写的“其上不皦,其下不昧,绳绳兮不可名,复归于无物。是谓无状之状,无物之象,是谓惚恍”;第16章“夫物芸芸,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,静曰复命。复命曰常,知常曰明”;第48章“为学日益,为道日损。损之又损,以至于无为”;第49章“圣人常无心,以百姓心为心”,以及反复出现的“道常无名”“道常无为”……文中反复出现的不、无、静等,讲的就是“无”,就是“道之体”。
如果说“道之相”的获得途径是“为学日益”,那么“道之体”的获得途径就是“为道日损”,损到你的“心”是“无”的。当你“心是无的”即“无为”的时候,就达到“万物一体”的境界,你才能不“自是、自见、自矜、自伐”,才能像水一样无常形,才能如22章那样“曲则全”,才能像15章善为士者那样随事应变、微妙玄通,才能做到老子不厌其烦教导我们的怎样“善(擅长)”。
“道之用”——“道之用”就是对“道之体”和“道之相”的融合、运用。《道德经》第11章列举了车、器、室三个例子来说明“用”,得出“有之以为利,无之以为用”的结论。通过以上的分析,我们知道,万物之“相”就相当于万物的“有”,万物之“体”就相当于万物的“无”。在《道德经》中,“道之相”就是“有”,“道之体”就是“无”,对“道之体”和“道之相”的融合,就是“道之用”。那么对道又是如何用呢?老子也有不厌其烦的教导,比如:第1章“常无欲以观其妙;常有欲以观其徼”;第4章“道冲而用之或不盈”;第5章“多言数穷,不如守中”;“第28章的“三知三守”;第40章“反者道之动,弱者道之用”;第42章“万物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和”;第45章“大成若缺,其用不弊。大盈若冲,其用不穷”;第48章“为学日益,为道日损。损之又损,以至于无为”;第56章“塞其兑,闭其门;挫其锐,解其纷,和其光,同其尘”;第63章“为无为,事无事,味无味”;第71章“知不知,尚矣;不知知,病也”……讲的都是对“道之相”和“道之体”的“用”。
需要注意的是:在万物和道中,“相的有”和“体的无”是普遍性的,和《道德经》第11章所列举的三个例子的“有”“无”是不同的。第11章所举的三个例子中的“有”和“无”其实都属于“相”的范畴,因为车子、器物、房室等的“无”虽然看不见摸不着,但它是可感知可意识的。包括我们有的学习者喜欢用“看到半个西瓜”的例子来说明有和无的关系,这个例子中的有和无也是“相”。我在《道德经演义(15)》就有特别强调,老子通过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“有”和“无”是为了证明出“有之以为利,无之以为用”这个理论的,并非是“器物空间之无”就是“道之无”,这一点要特别注意。我看网上有很多人对“无”和“有”争论不休,其实没有真明白,脑子里还是糊涂的。“相的无”虽然看不见、摸不着,但它随“相的有”而变化,有变化就是“相”。“体”的“无 ”是恒定的,“体的无”才是“道的无”。
这一点确实不好理解,所谓“悟道”其实悟的就是这一点。简化一点,大家记住“无”就是“心无所住”就行了。【皂罗袍3】先生有一个“空车装货”的例子,比喻得很恰当。
通过以上论述,我们把“道”的“名”“相”“体”“用”综合在一起,很容易得出“道”的全息图象。如果你认真读了以上的文字,我相信能基本理解和明白《道德经》中大部分概念和表述。比如“大”,既是“道”的别称,又是“道之相”的重要特征。再如“自然”,讲的就是“道之体”的本性。再如“冲”和“中”,讲的就是对“道之体”和“道之相”的融合运用。再如“损”和“益”,“益”的是对“道之相”信息的积累,“损”的是对积累的“道之相”信息的辨伪存真。再如“反者道之动”,就是从“道之相”到“道之体”的感悟;“弱者道之用”就是从“道之体”到“道之相”及“道之用”的生发。再如“无心”,就是用“心”融入“道之体”的觉悟……顺着这个思路,你就可以将所有的概念从“名”“相”“体”“用”四个方面进行解构,肯定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“相体用”或者“名相体用”适用于万事万物,可以作为我们日常的思维方法。所以老子说“吾道甚易知甚易行”而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,多数人只是“看”到了“相”,而不会用“心”去观照“体”,不会从“体”或“万物一体”出发认知万物,不会“无为”,导致的结果是凡事考虑不到变化,思维形成定势,从而自是、自见、自矜、自伐。
有些人学佛学道或有所感悟后,倒是明白了“凡所有相皆是虚妄”的道理,也知道了“空”和“无”是怎么一回事,但又陷入另一个误区,即对“相”一概否定和排斥,只相信“心”中的那个“空”或者“无”。比如有名的“幡动心动”比喻,有人就只相信“心动”,不相信“幡动”。佛性真空,不是不显现,因为起用必显现。假如空了没有相,即不是自性了。因为有心必有相,心就是相,相就是心,心相不二。镜子里一定有影子,没有影子不成为镜子,因为没有妙用,佛性就变为死空、顽空。“真空”和“妙有”是一事两面,是“有之以为利,无之以为用”的关系。《道德经》的道理是一样的,讲“体之无”,必伴随着“相之有”。有无相冲、相中、相和、相融,万事万物才有其“用”。
通过以上的分析,大家是不是觉得“道”一点也不神秘,“道”就在我们身边,老子所说的“吾道甚易知甚易行”之言一点儿也不虚,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之言一点也不妄,庄子说的“道在屎溺”话糙理不糙。
用“体相用”来指导我们的生活也是非常简便可行的法则。比如:一个人生活生存于世,同时有多种身份角色,不同的身份角色就是一个人的“相”,不同的“相”有不同的“用”,怎样才能“用”得好,那就要“不住相”,你的心之“体”永远保持“空、无”的状态,当领导的时候好好当领导,不要把当父亲的角色运用到当领导上;当父亲的时候好好当父亲,不要把当领导的角色运用到当父亲上;面对不同的境遇,你始终保持空杯心态,这就是“冲而用之或不盈”“不欲盈”“蔽而新成”“不如守中”“外其身”“身下之”“为而不争”……这些教导的含义所在。
明白了这个道理,再来读第15章描述的“善为士者”,第27章描述的“五善”,第28章描述的能“知”会“守”……就豁然开朗了。
佛教中“体、相、用”的概念和思维方法,给我们认知事物提供了三个维度。 但是对于“体、相、用”的理解,因为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清晰的梳理,误解和误用甚多。比如南怀瑾就认为:
……拿中国唐代以后佛学原理来说,万物只有三个理则——体、相、用。如这茶杯,玻璃为“体”,“相”就是它的形状,“用”就是它的功用,即是可以盛液体的东西。抽象的思想,也是一样。譬如我们现在讲的,以孔子的《论语》思想为“体”,“相”就是二十篇《论语》,我们来研究、解释。“用”是了解孔子以后,才知反对孔子错在何处,又该怎样去弘扬中国文化,其“用”就在此……
——《论语别裁》
这段论述与亚里士多德“事物四因论(质料因、形式因、动力因和目的因)”非常接近,而且理解起来也不难。十八世纪中国学界倡导“西学为体,中学为用”,其中“体、用”的含义与南先生的理解是一致的。截至目前,对“体”的理解基本框定为“质地、材质”的意思。这样理解不能说不对,却是与佛教理论是不符的。那么到底什么是“体相用”呢?
我们先从最容易理解的“相”说起。
“相”即万物表现出來的现象,物理现象、化学现象、生理现象、心理现象……一句话,凡是用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“六根”能感触、意识到的,都是“相”。有人认为看得见、摸得着、听得见的才是“相”,其实不然,“相”也有看不见、摸不着、听不见的,比如电子波。有人认为物质范畴才是“相”,其实也不然,思想、精神范畴也是“相”,比如人们总结出来的所谓“规律”就是“相”,人们闭着眼睛做的白日梦也是“相”。显然,事物的材质、质地也能看得见、感知得到,也是“相”。所以,南怀瑾所说“玻璃是体”就与佛教的理论不符。
有了“相”就有了“用”。
不同的相,有不同的用。比如黏土做成碗(相) ,就有碗的功用;做成杯子(相) ,就有杯子的功用;做成佛像(相),就有教化的功用。同一个“相”,也可以有不同的“用”,比如杯子,可以用来装东西,也可用来变魔术。
佛教理论中为什么说“凡所有相,皆是虚妄”呢?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“用”随“相”变,“相”不是固定不变的,相的用也不是固定不度的,变才是“相”的绝对性。这与《易经》的“三易即变易、简易、不易”以及马哲理论的“世界是物质的,物质是运动和变化的”都是同一道理。《道德经》第2章讲道“有无相生,难易相成,长短相形,高下相盈,音声相和,前后相随,恒也”,这句话的含义就是“相的变化是永恒的”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,只有变化是不变的。“变化”可以作为判断事物“相”的绝对标准。
理解了“相”和“用”,我们再来说“体”。
佛教认为,万法之本“体”,即为万法之“性质”。所谓“性”,系以“无改”为义,是不生不灭,永远不变,系所谓“法尔如是”的。《道德经》中说的“人法地、地法天、天法道、道法自然”、“莫之命而常自然”、“辅万物之自然”……中的“自然”,和“法尔如是”类似,说的就是不以任何因素而改变。所以,“不变”可以作为判断事物“体”的绝对标准。这一点理解起来比较烧脑,我们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:
一、从“体”与“相”“用”三者的关系上来理解。上文我们说过,“体、相、用”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三个维度,“相”是事物中“变”的因素,那么“体”就应该是事物中“不变”的因素。事物中不变的因素有哪些呢?有很多!比如“变”就是事物中不变的因素,所以“变”算是“体”之其一;《道德经》中所说的“自然”,即“本来就那个样子”(上文中佛教所说的“法尔如是”),也是事物中恒常不变的因素,所以“自然”也算是“体”……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“体”是“本体、根本”的意思。《道德经》第16章说“夫物芸芸,各复归其根”,就是从“相”归到事物的“体”上。
二、从认知主体的认知方法上来理解。“相”是认知主体通过眼耳鼻舌身意等感觉器官来认知的,而“体”是认知主体通过“心”来“体会”的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“体”是“体会”的意思。
三、从“用”的角度来理解。上面说过,“体”有“体会”的意思,离不开“心”。如果我们的“心”是一面镜子的话,这面镜子是用来观照“相”的,有心还必须有“相”,才能有“用”;反过来,“相”必须通过“心”才能示其形、尽其用。如果没有“相”,心的镜子功用也就发挥不出来了。有“相”还要“心空”,如果“心”是满的、脏的、垢的,镜子的功用也发挥不出来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“体”和“心”是分不开的。佛教理论所说的“体”指的是“空”,即“缘起性空”中所说的那个“性空”,这个“空”还需要用“心”去体会。学习过佛理的人不难理解,但没有学习过佛理的人理解起来还是不太容易。在哲学上这叫“形而上”。我们再不妨拿大家耳熟能详的“看山三境界”来进一步说明。
第一重境界叫“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”。这一重境界相当于对“相”的认知,即用眼耳鼻舌身意等感觉器官和山这种事物进行的信息交流,我们用的手段是“看”,获得的信息是“相”。
第二重境界叫“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”。这一重境界就不是用“看(六根)”了,而是用我们的“心”去“观”。有人就问是不是闭上眼睛用心去臆想山水形象的信息呢?不是的!没有那么简单!用“心”去“观”,就是用“心”去“悟”。“观”什么?“悟”什么?悟山水的本体、本质、自然、恒、常、根……即《道德经》16章描述的“致虚极,守静笃。万物并作,吾以观复。夫物芸芸,各复归其根……”
我们用苏轼的《题西林壁》来说明:
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
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这一首诗说的就是第一重境界,这重境界得到的信息是“相”,从“相”上得到的信息就是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。如果闭上眼睛去回忆之前“看”到的庐山景象(相),我们就能“识得庐山真面目了吗”?还是不能。那么怎样才算“识得庐山真面目”呢?那就是用“心”去“观”,体悟到“庐山”这种事物的“根”。我们要“观”到那个“庐山真面目”,就要达到“看庐山不是庐山”的境界,那才是庐山的真面目。那么庐山的真面目是什么呢?是变,是空,是无,是我心,是自然……
“观”到庐山真面目之“体”后,“心”中无庐山之“相”,只有庐山之“性”,这就是“性空”。如果某时某刻你眼前出现了庐山的一幅照片、一幅画,或者听某人讲起庐山,你“心”中的“空”就会变成“有”,这就叫“真空妙有”。
有读者就要“大笑之”了:按照你的逻辑,任何事物,除了“相”和“用”不同,“体”不就一样了么?
还真是这样的,能参悟到万物一“体”,才算真正理解了“体”,万物一体即万物一理,你就对“体相用”理解透彻了。
所以,“观”的结果,我们的心就能体会到万物的“无”,这就是“涤除玄览”,这个时候,心就“空”了。
如果你还不理解,就记住一点:万物的“体”就是佛教所谓的“空”,《道德经》所谓的“无”。当然还有另外一些说法也是“体”的补充意思,比如:根、常、恒、自然等,都是从不同角度的不同表述。
悟透了万物一“体”,第三重境界“看山还是山,看水还是水”就达到了。没有第一重境界的“相”,你不知道万物有何用,这一重境界让你“知其然”;没有第二重境界的“体”,你不知道万物为何用,这一重境界让你“知其所以然”。“用”是连贯“相”和“体”的纽带。为什么最高的境界是“看山还是山,看水还是水”?因为你不仅看到了山水之“相”,也看到了山水之“体”,“相”和“体”相冲、相和,才有了山水之“用”。“有之以为利,无之以为用”——“相”就是“有”,“体”就是“无”。到了第三重境界,就能“识得庐山真面目”了,苏轼的诗就可以改成这样:
横观自然侧自然,远近高低各自然;
识得庐山真面目,只缘我心亦自然。
这就是“物我合一”的境界,即“得一”。
用“体相用”来认知事物,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。比如对“水”的认知,水有三态,三态又可因环境变化而千姿百态,这是其“相”、其“有”、其“实”;而其“体”、其“无”、其“空”,需要用“心”来参、悟,从而达到“用”。
明白了“体相用”的思维方法,就会“心无所住”。比如你“心”中有杯子的“体”,即使你看到一个从没见过的杯子,也能立即判断出它就是个杯子,从而拿来所用;遇到一件从未遇到的新生事物,也能从“心”中的“空”和“无”中找出认知和行动的对策,这就是《道德经》中“无为”的根本含义,即“从体而为”,而不是从“从相而为”。
我们拿“体相用”来理解《道德经》,也会变得更加简洁容易。
在《道德经》中,老子就是把“道”作为一件事物来描述的。第21章“道之为物,惟恍惟惚”,第25章“有物混成,先天地生”,明确指出“道”就是一物。既然是一物,就是“万物”之一,就如同“杯子”一样,也是可以用“体相用”三维分析法来进行认知的。
那么什么是“道”呢?这是至今仍争论不休的话题,其实参与争论者都是站在不同的维度来各说自话,意见当然不好统一。如果用“体相用”三维分析法,事情就变得简单了。因为“道”作为万物之一,只有从“体相用”再加上一个“名”,从这四个方面统筹兼顾,思考的结果才是全面的、系统的。我们不妨从这四个方面一一论述:
“道之名”——每个事物都有一个名字,那么“道”显然也是首先作为一个“名”来使用的。第1章“道可道、名可名”就有这层含义。第25章“有物混成,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,独立而不改,周行而不殆,可以为天地母。吾不知其名,强字之曰道,强为之名曰大”。这句话说得很明白,“道“和“大”同为一种“物”的名字。“道”和“大”的关系就相当于一个人有官名,同时还一个反映其生理特征的绰号,比如张三,也叫胖子。那么“道”是哪种“物”的名字呢?我认为,“道”就是“万物”的名字。人生活、生存于世,要与“万物”打交道,这个过程就是与“万物”进行能量、信息和价值交换的过程。具体到“万物”其中之一种,比如杯子、车子、房子等,很容易理解。但人类和个体,面对的不是一事一物、百事百物,而是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的事物。这所有的事物用文字表达出来就是“万物”,老子给“万物”起了个“名”就叫“道”。另外,“大”“天、地”“人”等有时也可以代指“道”,因为它们是“道”的有机组成部分或“道”的某些重要特征。
“道之相”——具体的万物都有各自特定的“相”,那么万物这个集合体“道”的“相”是什么呢?谁能把宇宙万物的“全息图像”描述出来呢?上文我们讲了,如果你白天看了庐山,晚上回到家闭着眼睛回忆一下脑子中的影像,虽然你用的是“心”,但“看(幻想)”到的仍然是“相”。那么要“看”到“万物的相”就更不容易了。那我们来看老子是怎样表述的吧——《道德经》第4章“道冲而用之”,第14章“视之不见”,第21章“孔德之容”,第25章“道之为物”,描写的就是万物即“道”的“相”。这些章节的共同特点是“虚幻”,所以给读者带来极大的困惑。但是,如果你明白“道”就是万物,你怎样来描述呢?你闭目冥想,把你见过的没见过的万物都在你的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切换,你要用文字描述出来,不正是老子笔下这些虚幻、缥缈、恍惚的文字吗?知道了这个原理,就会明白老子的文字功底是多么雄厚。而且老子怕大家不明白,又用了具体的事物作比喻,如婴儿、谷、溪、朴、水、曲等来描述“道之相”的某一特征,我们把这些都综合起来理解,“道之相”不就显得很立体了吗?
“道之体”——前边已经讲过,万物的“体”就是一、是根、是常、是恒、是自然……归根到底,就是佛教所说的“空”,也就是《道德经》所说的“无”。第14章描写的“其上不皦,其下不昧,绳绳兮不可名,复归于无物。是谓无状之状,无物之象,是谓惚恍”;第16章“夫物芸芸,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,静曰复命。复命曰常,知常曰明”;第48章“为学日益,为道日损。损之又损,以至于无为”;第49章“圣人常无心,以百姓心为心”,以及反复出现的“道常无名”“道常无为”……文中反复出现的不、无、静等,讲的就是“无”,就是“道之体”。
如果说“道之相”的获得途径是“为学日益”,那么“道之体”的获得途径就是“为道日损”,损到你的“心”是“无”的。当你“心是无的”即“无为”的时候,就达到“万物一体”的境界,你才能不“自是、自见、自矜、自伐”,才能像水一样无常形,才能如22章那样“曲则全”,才能像15章善为士者那样随事应变、微妙玄通,才能做到老子不厌其烦教导我们的怎样“善(擅长)”。
“道之用”——“道之用”就是对“道之体”和“道之相”的融合、运用。《道德经》第11章列举了车、器、室三个例子来说明“用”,得出“有之以为利,无之以为用”的结论。通过以上的分析,我们知道,万物之“相”就相当于万物的“有”,万物之“体”就相当于万物的“无”。在《道德经》中,“道之相”就是“有”,“道之体”就是“无”,对“道之体”和“道之相”的融合,就是“道之用”。那么对道又是如何用呢?老子也有不厌其烦的教导,比如:第1章“常无欲以观其妙;常有欲以观其徼”;第4章“道冲而用之或不盈”;第5章“多言数穷,不如守中”;“第28章的“三知三守”;第40章“反者道之动,弱者道之用”;第42章“万物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和”;第45章“大成若缺,其用不弊。大盈若冲,其用不穷”;第48章“为学日益,为道日损。损之又损,以至于无为”;第56章“塞其兑,闭其门;挫其锐,解其纷,和其光,同其尘”;第63章“为无为,事无事,味无味”;第71章“知不知,尚矣;不知知,病也”……讲的都是对“道之相”和“道之体”的“用”。
需要注意的是:在万物和道中,“相的有”和“体的无”是普遍性的,和《道德经》第11章所列举的三个例子的“有”“无”是不同的。第11章所举的三个例子中的“有”和“无”其实都属于“相”的范畴,因为车子、器物、房室等的“无”虽然看不见摸不着,但它是可感知可意识的。包括我们有的学习者喜欢用“看到半个西瓜”的例子来说明有和无的关系,这个例子中的有和无也是“相”。我在《道德经演义(15)》就有特别强调,老子通过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“有”和“无”是为了证明出“有之以为利,无之以为用”这个理论的,并非是“器物空间之无”就是“道之无”,这一点要特别注意。我看网上有很多人对“无”和“有”争论不休,其实没有真明白,脑子里还是糊涂的。“相的无”虽然看不见、摸不着,但它随“相的有”而变化,有变化就是“相”。“体”的“无 ”是恒定的,“体的无”才是“道的无”。
这一点确实不好理解,所谓“悟道”其实悟的就是这一点。简化一点,大家记住“无”就是“心无所住”就行了。【皂罗袍3】先生有一个“空车装货”的例子,比喻得很恰当。
通过以上论述,我们把“道”的“名”“相”“体”“用”综合在一起,很容易得出“道”的全息图象。如果你认真读了以上的文字,我相信能基本理解和明白《道德经》中大部分概念和表述。比如“大”,既是“道”的别称,又是“道之相”的重要特征。再如“自然”,讲的就是“道之体”的本性。再如“冲”和“中”,讲的就是对“道之体”和“道之相”的融合运用。再如“损”和“益”,“益”的是对“道之相”信息的积累,“损”的是对积累的“道之相”信息的辨伪存真。再如“反者道之动”,就是从“道之相”到“道之体”的感悟;“弱者道之用”就是从“道之体”到“道之相”及“道之用”的生发。再如“无心”,就是用“心”融入“道之体”的觉悟……顺着这个思路,你就可以将所有的概念从“名”“相”“体”“用”四个方面进行解构,肯定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“相体用”或者“名相体用”适用于万事万物,可以作为我们日常的思维方法。所以老子说“吾道甚易知甚易行”而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,多数人只是“看”到了“相”,而不会用“心”去观照“体”,不会从“体”或“万物一体”出发认知万物,不会“无为”,导致的结果是凡事考虑不到变化,思维形成定势,从而自是、自见、自矜、自伐。
有些人学佛学道或有所感悟后,倒是明白了“凡所有相皆是虚妄”的道理,也知道了“空”和“无”是怎么一回事,但又陷入另一个误区,即对“相”一概否定和排斥,只相信“心”中的那个“空”或者“无”。比如有名的“幡动心动”比喻,有人就只相信“心动”,不相信“幡动”。佛性真空,不是不显现,因为起用必显现。假如空了没有相,即不是自性了。因为有心必有相,心就是相,相就是心,心相不二。镜子里一定有影子,没有影子不成为镜子,因为没有妙用,佛性就变为死空、顽空。“真空”和“妙有”是一事两面,是“有之以为利,无之以为用”的关系。《道德经》的道理是一样的,讲“体之无”,必伴随着“相之有”。有无相冲、相中、相和、相融,万事万物才有其“用”。
通过以上的分析,大家是不是觉得“道”一点也不神秘,“道”就在我们身边,老子所说的“吾道甚易知甚易行”之言一点儿也不虚,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之言一点也不妄,庄子说的“道在屎溺”话糙理不糙。
用“体相用”来指导我们的生活也是非常简便可行的法则。比如:一个人生活生存于世,同时有多种身份角色,不同的身份角色就是一个人的“相”,不同的“相”有不同的“用”,怎样才能“用”得好,那就要“不住相”,你的心之“体”永远保持“空、无”的状态,当领导的时候好好当领导,不要把当父亲的角色运用到当领导上;当父亲的时候好好当父亲,不要把当领导的角色运用到当父亲上;面对不同的境遇,你始终保持空杯心态,这就是“冲而用之或不盈”“不欲盈”“蔽而新成”“不如守中”“外其身”“身下之”“为而不争”……这些教导的含义所在。
明白了这个道理,再来读第15章描述的“善为士者”,第27章描述的“五善”,第28章描述的能“知”会“守”……就豁然开朗了。
《龚鹏程:中西论衡》
龚鹏程 著
中国画报出版社
龚鹏程不仅精于国学,亦是欧美现代后现代理论研究的先驱者。《龚鹏程:中西论衡》是龚鹏程未曾出版过的一部全新著作集,专题探讨了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异同与融合,29篇文章内容涉及文学、哲学、艺术、历史、法治、科学、宗教等众多方面,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。作者融通古今,横贯中西,引经据典,洞察深入,以西方为方法,论衡中西,把中土传统经世致用之学和欧美现代后现代理论结合, 应用于现实。
>>精彩试读
中国人不爱看相
人生天地之间,自居万物之灵,总觉得自己跟其他动物不一样,因此各民族都不由自主地发展出“人的自尊”思想。我国上古即讲天地人三才,老子也有“天大地大人亦大”之说,后来“天地之间,人为最尊”一类讲法,更不可胜数。其他民族也一样。希伯来民族不是说上帝以他自己的形相造人吗?人是上帝的仿本,地位当然远高于其他动物。
可是中国人的身体思维跟其他文明终究非常不同。
一、不以形体为崇拜对象的民族
(一)
像刚刚举的例子,就不难看出:我国讲人的尊贵,是从才德能力上说,希伯来则首先由形体说。这就是对“人”的思维有所不同。因这个思维不同,两大文明的身体观遂也不同。
(二)
古印度文明,亦极看重人的体相。
因此婆罗门之智能,就很强调相人之术。如《佛本行集经》卷三中云:“(珍宝婆罗门)能教一切毗陀之论,四种毗陀皆悉收尽。又阐陀论、字论、声论,及可笑论、呪术之论、受记之论、世间相论、世间祭祀呪愿之论。”所谓“世间相论”,与婆罗门五法中的“善于大人相法”,都是相术。可见相法是婆罗门极为重要的能力。
不仅如此,婆罗门还注重相貌容色。认为好的相貌必定由修行善法而来。
如一位婆罗门,在路途中看见了佛陀“姿容挺特,诸根寂定,圆光一寻,犹若金山”,便问佛陀:“本事何师?行何道法?以致斯尊。”(《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五)
佛典中叙及婆罗门时,也常说该婆罗门“颜貌端正,人所乐观”(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》卷十一)。诞生的小孩,如果“仪容端正,人所乐观”,就取名为“孙陀罗难陀”;如果形貌不扬,“具十八种丑陋之相,父母见已,极生不乐,名曰恶相”(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》卷二八)。小孩恶相,则不教授婆罗门之学,使他无法成为婆罗门。但一般所说的相貌端正,还不是婆罗门相法中最为人所看重的“大人之相”。
什么是大人相呢?要有32 种相貌特征,才能称得上是大人,如《中阿含经·三十二相经》所说。
汉译佛典的阿含部、律部、本缘部等较早集出的佛典中,多处记载婆罗门的三十二相说:足安平立、足下生轮、足指纤长、足周正直、足跟踝后两边平满、足两踝月庸、身毛上向、手足网缦似鹰、手足柔软、肌皮软细不着尘水、毛色绀青右旋、鹿腨肠、阴马藏、上下圆相称、手摩膝、身金色、两手两足两肩及颈七处隆满、上身大如狮子、颔如狮、脊背平直、两肩间满、四十齿、牙平、齿间无隙、齿白、齿通味、声悦耳、广长舌、眼睫如牛、眼色绀青、顶有肉髻、眉间生白毛。
这是古婆罗门所欣赏崇仰之形相,后来完全被大乘佛教吸收,用来形容佛陀之美。
(三)
古希腊亦甚重视人相问题。
亚里士多德《体相学》说:“过去的体相学家分别依据三种方式来观察体相;有些人从动物的类出发进行体相观察,假定各种动物所具有的某种外形和心性。他们先议定动物有某种类型的身体,然后假设凡具有与此相似的身体者,也会具有相似的灵魂。另外某些人虽也采用这种方法,但不是从整个动物,而是只从人自身的类出发,依照某种族来区分,认为凡在外观和秉赋方面不同的人(如埃及人、色雷斯人和斯库塞人),在心性表征上也同样相异。再一些人却从明显的性格特征中归纳出各种不同的心性,如易怒者、胆怯者、好色者,以及各种其他表征者。”可见体相学在希腊乃是源远流长的。
亚里士多德对以上各项观察体相之法均不以为然,因此他参考相士们的说法再予改造,云:体相学,就正如它的名字所说明的,涉及的是心性中的自然秉赋,以及作为相士研究的那些表征的变化产物的后天习性……相士不外是通过被相者的运动、外形、肤色、面部的习惯表情、毛发、皮肤的光滑度、声音、肌肉,以及身体的各个部位和总体特征来作体相观察。
依他的观察,软毛发者胆小、硬毛发者勇猛。若肚腹周围毛发浓密,则是多嘴多舌之征。而动作缓慢,表明性情温驯;动作快速,则表明性情热烈。至于声音方面,低沉浑厚标示着勇猛,尖细乏力意味着怯懦。雄性较雌性更加高大强壮,四肢更加健壮光滑,各种德性也更加优良。感觉迟钝者的表征,是脖颈与腿脚一带肥胖、僵硬、密实,髋部滚圆,肩胛上方厚实,额头宽大圆胖,眼神暗淡呆滞,小腿及踝骨周围厚实、肥胖、滚圆,颚骨阔大肥厚,腰身肥胖,腿长,脖厚,脸部肥胖且长。赌徒与舞者双臂皆短。心胸狭窄之人,四肢短小滚圆、干燥,小眼睛,小脸盘,像科林斯人或琉卡底人。由肚脐至胸脯比由胸脯到脖颈更长者能吃,胃口很好……
皮肤太黑者胆小,埃及人、埃塞俄比亚人就是这样。皮肤太白者也胆小,譬如妇人。肤色居中者趋于勇猛。黄褐色毛发者有胆量,譬如狮子。火红色毛发者狡猾,譬如狐狸。身体不匀称者是邪恶的,雌性就带有这种特性……
他这种相人术,明显带有性别、种族之歧见,在今天看,都是笑话。但无论如何,由其叙述可知古希腊相术之大凡。相法为时所重,故亚里士多德专门写了《体相学》一书以为斯学张目。
该书开宗明义说道:“身体与灵魂之间有相互作用的关系…… 在同一种类的动物中,必是有如外形则有如是心性。”故其体相学重在由形体观察心性状态,与婆罗门相人术有类似之处。
(四)
相对于古印度、古希腊,中国古代却是相人术最不发达的。
上古没有相术,相术起于《左传》文公元年(前626)左右,孔子同时代人郑国的姑布子卿。所以荀子《非相篇》曾批评:“相人,古之人无有也,学者不道也。古者有姑布子卿、今之世梁有唐举,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,世俗称之。古之人无有也,学者不道也。”
足证此术最早也仅能上推至姑布子卿,再往上找,就无渊源了。此法渐渐兴起,与相宫宅、相狗相马一般,为流俗所称,则是战国的风气,但地位在相牛相马之下。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相术,麻衣、柳庄之类,更都是宋明以后的东西。相士,属于下九流跑江湖的底层人,跟婆罗门、亚里士多德他们地位悬殊。
故这种看相的风气会惹来荀子的批评不足为奇。因为依中国思想的一般特征或重点而言,中国人是重内不重外的。
荀子说:“相形不如论心、论心不如择术。形不胜心、心不胜术。”其实非他一家之私议,即使后世论相面相手相形体者,也仍要说“相由心转”。庄子《德充符》载各种德充于内而形貌丑陋畸形的人,更可以显示思想家对体貌体相不甚重视。
庄子这类说法,在婆罗门或亚里士多德那儿,就都是不可想象的。因为依他们的看法,外形与心性是相合的,外貌丑陋者,心性也必不美不善。庄子荀子则相反。荀子说:“仲尼之状面如彭蜞。周公之状身如断菑。皋陶之状,色如削瓜。傅说之状,身如植鳍。伊尹之状面无须眉。禹跳、汤偏。”圣贤都长得难看,坏人却不然:“古者桀纣长巨佼美,天下之杰也;筋力越劲,百人之敌也。今世俗之乱君,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。”因此他们主张不必论形相之美恶。
二、不以人体为审美对象的民族
比较东西方的体相观是非常有趣的事。苏美文化、古希腊、古印度都有造相的文化,或以铜铸人面、人首、人身,或以石雕,或以塑相,十分普遍。但在中国,出土千万件青铜器,除了三星堆有人形及面饰之外,绝不见铸像人体者。上古石刻也不见人相雕石,祭祀则用木主,不立图相、不塑人形。
故古希腊、古印度是造相的文化,我国是不造相的文化。
且古希腊等文化雕塑人体,以为美善之欣赏崇拜对象,这个观念或行为在中国亦绝不存在。
这些古文化的差异,即本于彼此不同之体相观。
中国不但不像古希腊、古印度那么重视体相之美,认为应重心而不重形;甚且我们认为形体非审美之对象,衣裳才是。赤身露体,那种原始形体,相对于衣裳冠冕黼黻,乃是可羞的。因为衣裳等才是文化,赤身则如动物那样,是非文化、无文化的样态。故赤身跣足肉袒以见人,若非羞辱自己便是羞辱他人。如廉颇向蔺相如左袒负荆请罪,就是自居罪人;弥衡裸身肉袒击鼓骂曹操,即是用以羞辱别人。
我们不曾有过人体艺术;自古崇拜天神、人王、父祖,也都不塑相。制俑者更被孔子批评,谓其“相人而用之”,甚为缺德。是人不必相、不可相,相亦无意义也。后世塑相造相之风,乃受佛教影响。
换言之,中国体相观的特点是不重形相之美,亦无人身形相崇拜(为了强调这一点,往往会故意说丑形者德充、形美者不善)。第二个特点是形德分离,“美人”未必指形貌好,通常是说德行好。三是不以形体为审美对象,而重视衣裳之文化意义及审美价值。
>>作者简介
龚鹏程,1956年出生于台北市,祖籍江西吉安。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,台湾南华大学、佛光大学创校校长,获台湾中山文艺奖、中兴文艺奖、杰出研究奖等奖项及台湾校园十大名师称号。2004年起,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、北京大学特聘教授,山东大学讲座教授。
主要著作有《文学散步》《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》《书艺丛谈》《国学入门》《龚鹏程四十自述》《中国诗歌史论》《中国文学批评史论》《侠的精神文化史论》等160多种。
作者:龚鹏程
编辑:金久超
copyright © 2022 一生命运网 版权所有 辽ICP备2022007116号-4
法律声明:本站文章来自网友投稿,不代表本站观点,版权归原创者所有,如果侵犯了你的权益,请通知我们,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!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