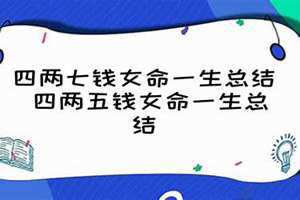
本文目录一览:
传说,有个将死之人,夜里做梦,自己被黑白二使带到了阴司森罗殿。阎君拿过生死簿一看,原来是同名同姓的两个人,遂叫黑白二使送还阳间。这个人第二天醒来,不觉精神百倍,病也好了。家人深感奇怪,问其缘故,那人极力回想,却只记得森罗殿外的柱子上写着一副诗联。
左边写的是:万恶淫为首;
右边写的是:百行孝居先。
自古道,父有教诲恩,母有怀胎苦。不论你是贫的、富的、贵的、贱的,孝顺都应该放在第一位。你看那古代的判罚中,忤逆不孝,重则斩首。
那么说,淫又何该是万恶之首呢?其实很好解释。不管他是读书的君子也好,贞良的妇女也罢,一旦动了贪邪好色的心,九头牛也难拉回来。不是有那么一句适才么,叫:只因世上美人面,改尽人间君子心。
看官们该说了,废话真多。(/偷笑)
话说,镇江府丹阳县偏远的一个乡里,有个叫仁善村的村落,村上有个叫魏化的佃户,妻子陶氏,靠佃主人家的三亩薄田养家糊口,日子过得清贫,却很充实。陶氏替他生养了两个儿子,长子魏大,次子魏二,没啥本事,也都跟着老父亲种租田。后来兄弟俩相继长大,魏大娶了一个工匠家的女儿,很是孝顺。魏二不肯娶农家女子,整天围着母亲吵闹。
这天大早,一家人正忙着脱米壳,老魏突然站起身来对陶氏说:“老婆子,我听说前村有个姓施的人家,好像有个闺女;听说年纪跟二郎相仿,还很勤俭咧;像什么插秧啦、踏车啦、积麻啦、纺纱啦,啥啥都会;你说,要不要请顺拐子去作个媒,完了咱俩这一桩心事?”
陶氏倒没什么意见,旁边的魏二不干了,接过话来嚷着说:“啥?叫我娶施家的大闺女?你们怕是不知道吧,他家的闺女又麻又黑又蠢;我就算这辈子不讨老婆,也不要她这样的歪货!”
母亲陶氏捱着他说:“那你说说,想找个啥样的?”
魏二想了想,说道:“也不说貌似天仙吧,起码不能是个俗家妇人。”
“咱这样的乡下人家,哪有你说的女子?再说了,就算有,能看上你吗?”老父亲没个好脸的说道:“别白日做梦了,去把门口的新米扛上,给城里主人家送去,就说是抵今年的田债。”魏二不敢反驳父亲,只得乖乖去城里送米。
古时候老百姓耳朵交通方式,几乎就是靠双腿走路。影视剧里动不动就骑马,乘马车,那都是骗人的。从晚清往前数,马是不允许老百姓随便骑的,只要当兵的,当官的,公务紧急的可以骑。有钱的老百姓骑驴,或乘驴车;没钱的就是地上走,甚至还得推个独轮车。
好在仁善村离丹阳城不算太远,约莫也就二三十里。年轻人体格好,就算扛上一包米,一天也能跑两个来回。
说来也巧,魏二来到主人家时,正赶上家主婆发飙,揪住一个丫环的头发疯狂输出。被打的这个丫环呢,叫桃花,白白净净,还挺标致。家主婆见有人来,这才松开手,但嘴里还依依不饶的放着狠话。别看桃花是个下人,有股子倔劲儿,这也是她屡屡挨打的原因。魏二撂下手里的米袋,简单交代了几句,跟着桃花出来了。桃花在前边跑边哭,魏二在后边躲边追,来在了一条小河边。
耳听得桃花喃喃自语说:“人活在世,哪个没头没脸?三天两头挨打,还不如一死百了的好。”
魏二见势不妙,赶紧上前拦着,并劝说:“我看你有吃有喝的,何必轻易寻死觅活?”
桃花哭着说:“你哪里晓得我吃的苦?上管头,下管脚,不是打,便是骂;前两天家主公不过偶然对我笑了一笑,家主婆就怀疑起来了,三天挨了她九顿打;你说我苦也不苦?”
“我本以为城里人日子都过得舒坦,没想到也有你这般苦命的人。”
“城里人如何?哪像你们乡下人,自由自在过日子。”
听她这么一说,魏二登时眼前一亮,忙问:“唉~你有对头了么?”
“什么对头?”
“对头就是.....你有许配人家吗?”
“没有;像我这样的丫环,身子骨不值钱,哪有人看得上我?”
“太好了;我问你,你是想嫁在城里呢?还是要到乡下去做个自由自在的人儿?”
“城里有什么好的?乡下僻静,如何不比伺候主家婆强?”
魏二嘻笑着脸问道:“不怕跟你说心里话,其实我正想找个城里人做老婆哩;不知你愿意跟我吗?”
桃花两边看了一看,见没人来,也就低声的回了一句:“你若真的有心,那我就嫁给你。”
“太好了太好了!”
“只不过,我是被卖到主人家的,身价十两银子,不知你能不能出得起。”
十两银子,对于魏二来讲,可谓巨款了。桃花见他面露难色,连忙又说:“你要是拿不出来,也先别着急,我这儿有些私房钱,能给你凑个数。”
说着,从腰里掏出来一个小荷包,里面零零散散装了五六两。
魏二接过来,说道:“你放心,我这就回去凑银子。”
“你可千万要来呀;到时候你去找家里的王阿叔,他会进去对我说的,不要忘了。”
“一定一定。”
魏二连蹦带跳的跑回家,把适才之事,一字不差的告诉给了爹娘。他父亲说:“好是好,但她毕竟是个城里人,乡下房子怕她住不习惯。”
“爹呀!这你就不要管了。”
事已至此,老两口也不好再说什么。把家里能典的家什都当掉,好歹凑了七八两银子,让魏二拿着去了。
王阿叔把他的来意告知家主婆,家主婆反倒开心了,追出来说:“魏二郎也是咱家的佃户,既然看上了桃花,也甭说十两银子,就拿六两的茶礼来就行。”
其实不单单是家主婆开心,魏二和桃花也开心。家主婆高兴的是,终于拔了这颗眼中钉;魏二高兴的是,终于如愿娶了城里的妻;桃花高兴的是,终于可以逍遥自在去了。
简单来说,茶礼一过,几个亲戚热热闹闹把桃花接到了乡下仁善村魏家。
一乘小轿,三四个吹手,就在魏家的草房里拜了堂,乡邻亲叙们纷纷前来吃喜酒。老父亲魏化因为连续两天忙碌,又兼多喝了几杯酒,不等众人散去,他先回房睡了。
魏二大喜的日子,自然要多喝几杯。等他把宾客们都送走,这才回屋圆房。桃花呢,只道是嫁到乡下自由自在,却不知他家住的是草屋,不是牛屎臭,定是猪粪香,房里连个窗户都没有,又气又闷。更可气的是,连个茅房都没有,濠野里随意大小便。
尽管如此,桃花也是强忍着没发火,您道是哪件事?
您说,家主婆若只是怀疑她,能连续三天对她拳打脚踢吗?还不是其事为实?再说魏二,虽然是个乡下人,但既有精壮的身板,又是个童男子,她也就暂时默认了。
赶等到了第二天,陶氏起来收拾院子,这才发现,老魏连个呼噜声都没打。
“当家的,当家的!人都下田了,你怎么像死狗一样还睡?”见他不回应,陶氏走到床前一推,整个人都硬了。“呀哟~老头子!你这是咋了?”
这边吓得陶氏号啕大哭,那边魏大两口子听见了,兜着裤子跑了出来。一家子问来问去,也不知是什么缘故,因为头天晚上还好端端的,都在一块儿喝酒呢。
甭管怎么着,人肯定是没气儿,商量商量后事吧。母亲陶氏边哭边说:“先前为了给二郎娶妻,已经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,如今连个买棺材的钱都没有,你们哥儿俩说说,咋个办?”
桃花一听,不高兴了,嘴里哝哝着说:“什么叫为了给二郎娶妻,花光了钱?难道说,你老公死了,还要来埋怨我们不成?”
“媳妇不要误会,我老婆子不会说话,你别往心里去;如今你父死了,要紧的是给他办后事,也不是为了这三五两银子。”
“反正我是没钱,我的钱也都给你儿子了。”
魏二插了一嘴:“实在不行,就去前面许家庄上找何敬山,跟他借几两印子钱,先买棺入殓再说别的吧。”
印子钱就是现在人们口中所说的。这个东西早在商朝的时候就出现了,只不过当时没有“印子钱”这个名词。明清时期管它叫“印子钱”,又专门儿放贷的财主,而且是合法的。假如说,有人向财主借了十吊钱,一月为期,每月利息二分,到一个月头上,连本带利还上,理论上来讲,就应该是十吊零二百文。什么是?就是不按常理出牌。十吊零二百文除以三十天,每天要还的钱款就是三百四十文。当然了,不管是按月还款,还是按天还款,每还一次钱,都会在折子上盖个印记,这就叫“印子钱”。
魏大接着说:“我跟你一块儿去,以后咱俩合力还。”
“行,事不宜迟,咱现在就去。”
哥儿俩一路来到了许家庄上。何敬山正忙着算账呢。魏大上去打了声招呼说:“何阿叔这两天生意好,忙得紧哩。”
何敬山抬头一看,说道:“魏二老,恭喜了;什么风把你们兄弟俩吹到我这儿来了?”
魏二说:“何阿叔,恐怕说出来你不肯信,天底下还有这样的怪事。”
何敬山打趣说:“甚怪事?莫非新娘子是个石女么?”
“不是;昨天晚上我才做了亲,今天早上父亲便好端端的死了,你说怪也不怪?”
何敬山吃了一惊道:“昨天我还见他在城里请和合纸呢,今天就死了,果然是怪事;那你们弟兄来我这儿,是有什么事吗?”
魏大说:“实不相瞒,家里刚办了红事,没有余钱买棺材,所以要找何阿叔借几两印子钱;就算我们弟兄俩合借的,后来共同偿还。”
“要几两?”
“四两。”
“一副棺材用不了这么多吧?”
“棺材是用不了,但后面还要请人做法事,少不得一二两银子。”
“这样吧,今天先给你俩拿二两五钱,先把棺材买回来;等到后天,我亲自到你家走一趟,把这一两五钱送上,顺道拜上一拜。”
“好好好。”
何敬山给写了张借款条,约定十个月连本利清还,兄弟俩签完字,拿钱出来了。至于哥儿俩如何买棺木,如何入殓,这里就不细细赘述了。
单说第三天清晨,魏大对魏二说:“二郎,咱在何敬山家借来的钱,还剩下一些,如今大家分了,明天我去别处另租几亩田,这边的几亩田,就留给你两口子种吧。”
魏二问说:“娘咋个办?”
“娘暂且住在你这边,我每个月给你拿盘缠来,就当是咱俩合养。”
母亲陶氏听见,垂泪说道:“如今你爹没了,我就开始吃素修行了;你们哥儿俩给我请一轴观音菩萨来,每个月贴点儿柴米,其他啥也不用管。”
桃花哝道:“做张做势,有粥吃粥,有饭吃饭,吃什么素,修什么行。”
一家子矗在原地,半句话不肯说。转天过来,魏大收拾好行囊,到仁善村外的十四五里处,租了三间草房,十亩田,两口子自己经营不题。
魏二见大哥搬走了,两口子又是买鱼又是买肉,整天就是受用作乐。然而大家都知道,他俩手里就那么几吊钱,花不了几天。
果不其然,一旬过后,手里没钱了。魏二是农户出身,自然扛起锄头下地干活儿。桃花不愿意去,就对他说:“我们城里人都是不种田的,有这等力气,进城做些生意不好吗?”
“娘子说得是,我明天就上城里做生意去。”
两口子商议定了,写下一张退田契,把田退了,干去了贩鱼的买卖。还真别说,卖鱼就是比种地挣钱,而且每天都有钱进账。
这天上午,债主子何敬山晃悠悠来到魏家,隔着柴门喊道:“有人么?屋里有人没有?”
“有人有人。”说着话,从屋里走出来一位妇人,头梳的整齐,顶上扎一块儿孝髻,身穿白布衫,玄色绸的背褡。白绢裙褶,漂白膝裤,一看就是正在守孝的人。没错,此妇人正是桃花。
桃花低着头一睃,问说:“你是何阿叔么?”
“正是。”何敬山打量一番后,接口问道:“娘子可是魏二的夫人么?”
“正是。”
“你们家之前借的钱,昨日就该到日子了,我也没让人来催,今日正好打这儿经过,顺便问问怎么回事。”
“呀哟~何阿叔不知道,我家魏二这不是刚做生意么,忙里忙外,啥都顾不上,因此耽误了还钱的日子;如今还要劳烦何阿叔亲自来要,真是不好意思;来来来,快到屋里坐坐,吃杯茶再走。”
正如桃花之前所说,她是城里人,什么样的人没见过?单从每个人的着装上来看,便能断出此人贫富。那何敬山呢,头戴京骚玄缎帽,身穿黑油绿绸衫,绫绸的绵袄,衫子衬里,无不鲜艳;再往底下看,脚着漂白绵袜,外蹬玄色辽鞋,白面盖子三牙须,齐整无比。
何敬山心里想的是,这种乡间地头,居然还有如此俊俏的妇人。
桃花心里却想的是,这种乡间地头,居然还有如此锦簇的汉子。
正当二人看对眼的时候,屋里又出来一位。母亲陶氏刚才在屋里拜佛,拜完才出来接着。“二娘子,你先进屋去,我陪何阿叔说说话。”
何敬山目送桃花进去后,这才站起身来说:“老亲娘,等魏二舍回来,你千万要跟他说一声,我还要去别处,就不打扰你们了。”
人就是这样,甭管心里中意的是什么,是个东西也好,是个人也好,一旦看对了眼儿,心里就跟有个痒痒挠似得,时不时挠你的痒痒。这不,何敬山连称呼都改了,可见心术不正。
等傍晚魏二回来,陶氏一把拉他过来说:“今天何敬山来咱家要印子钱了。”
“娘您放心,我腰里有,明天给他送过去。”
不料桃花就在门后,这厢闪出来接道:“送什么送?让他自己来拿就行,你再送过去,不是又耽搁一朝的生意吗?”
“娘子说得有理;我把钱放家里,明天等他来拿便罢。”
当夜无话,各自歇息。
转天醒来,陶氏在观音前点香拜佛,桃花则搬了张凳子坐在门口来回观望。不多时,何敬山果然又来了。桃花心生一计,把家里的一只鸡藏在柴堆里,嘴里却囔囔道:“你这老婆子,单吃粮,不管事,家里的鸡都不见了,你也不说找一找。”
陶氏在屋里听见了,慌忙来找,门里门外不见个影儿,只得一步步到坟里去寻。
何敬山老远看见,就问她说:“二娘子,在场上干啥子哩?”
桃花答道:“家里的鸡不见了,我在这儿寻鸡。”
“家鸡只在家里,若是野鸡,一定会去寻野外的食儿。”
桃花把他瞅了一眼,说道:“眼前的食儿不够吃,家鸡也要到野外去吃哩。”
话里话外,何敬山也听出了门道,低低的问道:“我来向魏二舍讨银子,他在家么?”
“不在家,但是银子在我这里。”
“你婆婆怎么也不在家吗?”
“我让她到坟里找鸡去了。”
“既如此,那你带我进去秤银子吧。”
正当二人在屋里说笑时,只听得陶氏咋咋呼呼回来了。桃花怕露了马脚,小声说道:“你快从后门走,银子明天再来拿。”何敬山也怕惹是非,慌慌张张溜了。
又过一天,何敬山早早来到家里,陶氏刚要做饭,看见了,忙叫道:“二娘子,何阿叔来讨银子了。”
桃花应道:“怎么来的这般早?”
何敬山还是假模假样的问话:“魏二弟在家么?”
陶氏回说:“卖鱼去了,银子在二娘手里。”
桃花听了很是不乐意,埋怨道:“银子是他们弟兄俩合借的,为啥要让我们先还;你这个当娘的也忒欺心了,单吃二媳妇;你现在就去对大儿子说,让他也凑一点来。”
按道理来讲,这话说的没毛病。但是在桃花心里,可不是这么想的。如今何敬山就在眼前,赶紧把老太太撵出去,才是称心如意的目的。
陶氏可能也觉得不妥,只能应承道:“我这就去说。”
“你到他家正好中午,吃他一顿午饭,也不为过;我这儿给你做两个饼,路上当个点心。”
至于陶氏走后,他俩个如何作孽,就不消细说了。
前面说过,魏大在仁善村外的十三四里处,租了田宅。陶氏一大早没吃饭,拿着两个饼去了。约莫走出去四五里路,脚下累得生疼,便在一个林子里停了下来。旁边有一块大长石头横着,她就坐在上面念道:“观世音菩萨,这小脚走路慢,实在走不动了。”
说着,就从兜里摸出来一张饼,想要吃了再走。只见这饼是又冷又硬,跟石块没什么两样。不禁又念道:“观世音菩萨,我老人家怎么吃得了这个饼?”
说犹未了,只见一个道姑走到跟前,对她施了一礼,说道:“老人家,我赶了许多路,腹中饥饿难耐,可否把这饼给我吃?”
“不是我不让你吃,就是这饼冷硬难吃,不敢怠慢了你。”
道姑说:“我饿极了,就算是冷的硬的,也没关系;我愿意用这背褡换你的饼,不知你肯慈悲否?”
“你要觉得能吃,那就给你吃吧,背褡却是不能要的。”
“老人家,我生平从不肯白吃别人的东西;你别看这背褡织的漂亮,也不是值钱的货物,权当我的一份心意吧。”
说着,就把篮子里的背褡,放在了陶氏的腿上。
陶氏又要推辞,道姑言辞恳切的说:“老人家,你若不肯拿我的背褡,那你这饼,我是宁死不会吃的。”
“好好好,我拿就是,这两个饼都给你吃。”
道姑接过饼来,三下五除二,吃了个干干净净。岂料,方才下咽,便听得大喊一声,倒在了地上。陶氏见状,赶忙去看,谁知那道姑已是七窍流血而死。
陶氏吓得面如土色,口里不住的说道:“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,这道姑为啥突然就死了?难道是饼子又冷又硬,吃坏了咽喉吗?这可怎么办?不行不行,趁着没人看见,我还是赶紧走吧,省得惹是招非。”
再说家里的贼男女,原文所述如下:
一个是偷汉子的都头,一个是撩妇人的宿积。
一个恣意的不休,一个尽情的出力。
一个是舍了缘砖抛黄金,一个是撇了家鸡偷野食。
一个在柴仓窝里逞风流,一个在粪扫堆边矜出色。
时至傍晚时分,门外突然传来一个声音,说是:“我回来了。”
桃花大吃一惊,说道:“这个分明是婆婆的声音,难道是她的魂魄来找我复仇了吗?”
且不说何敬山一溜烟儿,再次从后门逃走,但问桃花为啥这般惊讶。
原来是她使得伎俩。您想啊,她一个好吃懒做的妇人,平时连锅灶都不碰,哪会好心给婆婆做饼?难怪做出来的饼又冷又硬。至于这饼嘛,里面加了砒霜,目的是杀人嫁祸。可事实是,陶氏安然无恙的回来了,能不吓人么?
打开门一看,果真是婆婆陶氏;只见她手里拿了一条背褡,有气无力的说:“我走累了,快给我取条凳子来坐;老来没用,吃力得紧。”
桃花把凳子拿过来,指着她手里的背褡问道:“这是哪里来的?”
陶氏便把刚才发生的一切,都跟他说了。桃花愤恨不已,心说:天杀的,本来是给你吃的饼,偏偏叫别人吃了;这下可好,你没死成,反倒摊上一条人命。
陶氏把手里的绒背褡递过去,说道:“这个背褡给你穿吧,反正也没人知道,你别害怕。”
桃花接过来,看了又看,感觉绒背褡鲜艳无比,煞是好看,遂将其披在了身上。哪成想,背褡越来越紧,桃花的两眼定了神,形色如狂,“咕咚”一声跪在观音佛前,念道:“是我心毒,贪淫好色,为了跟何敬山永结私好,不惜下药毒害婆婆。”说完,身子往下一缩,竟变成了一只肉色大狗。
陶氏听了媳妇的自述,亲眼目睹了变化的过程,嘴巴张的老大,吓得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传闻一时四散开来,邻舍村坊的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纷纷围过来看热闹。有说是忤逆不孝的结果,有说是偷汉的下场。总之,说什么的都有。
正当喧闹之际,魏二挑着担子回来了。陶氏把事情对儿子细说一番,惊的魏二不敢相信。那只狗看见魏二,摇头洒耳的跑过来,只管叫,却是不能讲话。
这不废话么,都已经变成狗了,再说人话,那跟妖怪还有什么区别?
魏二叹了口气,说道:“万万没想到,你竟有这种歹心;背着我偷汉就不说了,还想药死婆婆,真是天不容,地不载,做狗也是便宜了你?”
陶氏问他:“如今把她养在家里,观者如市,也不像个样子,咋个办?”
“还能咋个办?把它丢到野外,随它生死罢了。”
“那怎么行?好歹是一条生命,万一落在屠宰的手上,岂不等同造孽么?依我看,把它送到放生庵,再念些经来超度的好。”
魏二应了,把狗带去庵里不题。
再说何敬山,自后门逃回之后,冒了些风寒,染上阴症在家。本来不是什么大病,恰恰有人来对他说,魏家的媳妇变成了狗。吓得一跳,夹惊伤寒,病重了。也就三四天的光景,死了。
说起何敬山,其实也就许家庄上一个乡宦的管家。许家听说他死了,便把他妻子常氏叫来,问她账目的事情。常氏年纪不大,也就廿五六岁,为人伶俐,账目一一交付了上去。
家主算来算去,总是不够账,便问说:“这账不对啊,怎的还少一百多两本钱呢?”
那何敬山最好包婆娘,常氏不是不知道,惟今之计,只得把首饰、家具、房田等等,连夜变卖,算是盘清了家主的账目。常氏呢,丈夫死了,家产也没了,膝下连个一儿半女都没有,孤零零一个人,不知要往哪里去流浪。
光阴如箭,不知觉又过了年余。常氏虽然独自守寡,却也时常想起以前的旧账,近来手头不太宽裕,便想着去前村找魏家兄弟讨债。魏二呢,自从妻子变成狗,送去放生庵之后,就与母亲陶氏一同居住,而且更孝顺了。每天贩鱼回来,也跟着母亲念佛吃素,日子过得不差。
这天,魏二陪母亲正在吃饭,常氏带着一身孝进来了,问道:“这里是魏家么?”
陶氏答:“正是。”
“何敬山是我的丈夫,我记得你们家曾借走了四两银子,我因为丈夫故世,也没上门来要过;今天忽然想起来,想与你们算一算。”
魏二站起身,说道:“银子是该给你的,不过你来的急,没那么多,只能先还你些利息。”
常氏言道:“不瞒你说,我现在也是一个人挑门,平时就靠纺绩赚点钱过日子;我知道,银子是你们兄弟俩一起借的,劳烦你跟魏大说说,看能凑多少。”
“何阿婶,你先坐下喝茶,我这就去说。”
魏二出门去了,就留下常氏和陶氏在家闲聊。
常氏问说:“我听说你家二娘子有一桩奇事,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”
“唉~说起来,都怪她动了淫恶的念头;当初你丈夫来家要债,他俩为了支开我,不惜在饼里下毒,险些要了老身的性命;幸亏佛菩萨显灵,才把她给收拾了。”
常氏叹了口气,说道:“我丈夫的性命,又何尝不是送在她的手里?”
“是啊,好端端的一段姻缘,就这么毁了。”陶氏抹了一把眼泪,接着说道:“等再两年,手里攒些钱,还要替二郎寻个对头,完他的终身之事才好。”
“该着如此。”
“对了,不知何阿婶有儿子吗?”
“没有。”
“难道就没想过改嫁他人吗?”
“我这般妇人,谁能看得上?再者说,丈夫才去世年余,且过些时日说吧。”
俩人聊得热火朝天时,魏二回来了,对这着常氏说:“我阿哥的一半有了,本钱二两,利钱五钱,还有五分,隔两三天就给您送来;您看,是不是要在原来的契约上,写一笔呀?”
常氏说:“我不识字,烦二舍替我写,我画个十字便罢。”
魏二给写张字据,常氏拿着钱走了。
回过头来,陶氏对儿子说:“我刚才跟何阿婶聊得兴起,也问了她的年纪,跟你差不多,而且无儿无女,人又踏实能干,配你为妻,也不枉一桩好事。”
“可拉倒吧;她是大户人家过来的人,吃喝不愁,受用不尽,咱家庙小,哪儿能容得下这尊大佛?还是把账算清,一别两宽的好。”
母亲见他这么一说,也不好再往下讲了。
转眼两天期到,魏二凑足了本利,来给何家送钱。常氏正在门前纺纱,一看魏二来了,急忙起来接着:“二舍来了,快快到屋里来坐,我这就给你沏茶。”
“何阿婶不必忙碌,我把银子给您送来就走。”
也不等常氏多说两句,他把银子撂下就要走。魏二往回一转身,正好撞上一个熟人。那人问他:“哟~这不是魏二舍么,你来何家做甚?”
魏二根本没驻足,边走边说:“我找何阿婶说两句话儿。”
“来都来了,不坐一坐吗?”
“没工夫。”
眼看着魏二走远了,那人趄在何家的矮墙上问常氏:“何阿婶,魏二来什么呀?”
常氏说:“他来还我些旧账。”
“如此说来,何阿婶手头可是肥泛了。”
“二三两银子,什么肥泛不肥泛的。”
看官,您道说话的这位是谁?原来就是惯卖狗肉的王二。他是个破落户,也没钱贩狗肉,就在村里闲荡,看见没人要的狗,就抓来杀掉,而后卖肉糊口。
眼下听得常氏露了二三两银子的话,登时动了念头,接着话说:“你一个人过日子,又没个使钱的地方,二三两银子怎么着也够花个把月了。”
常氏知道他的为人,不愿多做纠缠,自顾自的纺纱,不回应。王二见她不理不睬,扭过头来,哼着小曲儿也走了。
赶等到了二更天时,月明如昼,王二蹑手蹑脚的再次来到何家门前。四处看了看,确定没人,拿出小刀来撬门。
常氏住的房子呢,屋里屋外都很简陋,唯独这扇大门结实。王二撬了半天,也没能把门打开。动静声越来越大,常氏被惊醒了。也不敢问话,生怕歹人闯进来行凶。于是隔着门缝往外瞧,月光之下,王二的模样照的清清楚楚。常氏心说:不好,他这是见财起意了,眼下如何是好?
她是惯纺纱的妇人,墙上时常挂着一根绳子。常氏顺手把绳子取下来,就在里边把门闩绑在了一起。王二发觉不对劲,干脆也不撬了,用尽蛮力往里撞。闩是打开了,但是因为里面有一条绳子绑着,两扇门分不开,只有一条缝隙。
王二比划了比划,先把一条腿伸到了门里,想趁机钻过去。没想到常氏手里拿了一根木槌,照着左脚就是两棍。那王二被打得哭爹喊娘,摔得头晕眼花,口里恨恨的说道:“真是偷鸡不成,反蚀了把米。”
过不多久,天也亮了,常氏就把晚上发生的事儿,一五一十告诉了近邻们。邻居们说:“你何阿婶一个人过日子,难免有这般出境,放宽心。”
所谓,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常氏听在耳朵里,心里很不是滋味,自言自语道:“昨晚倒是把他打跑了,倘若这天杀的脚好了再来,我可怎么办?自古道,守寡的门前是非多,不是我没廉耻,还是得找个对头才行。”
正思量时,门前又来了一位熟人,常氏招呼道:“老顾,你这是往哪里去?”
顾拐子答:“正是来找你的;魏大舍不是还差你五钱银子嘛,叫我来还你;昨天二舍去家里说了,今天给你凑来的。”
常氏说:“你们魏家二舍都是这样至诚么?”
“大舍向来至诚;二舍也比往前不同了,既孝顺老娘,做人又老实,卖鱼还赚钱;这不,家里富裕了,租的田也多,雇我来给他家帮忙呢。”
“这么好的日子,二舍就没想再寻个对头吗?”
“二舍说了,等忙过了这几天,冬天闲了,再考虑对头的事。”拐子顿了顿,又说:“我还听他说,不论头婚二婚,只要会过日子,不忤逆就行。”
“是啊是啊。”
拐子越说越高兴,干脆嘻着脸问道:“依我老头子说,何阿婶没儿没女,论节妇牌坊,可能是天方夜谭了,还不如就近嫁给二舍的好;你看他人又不粗蠢,又后生,又勤俭,又和气,你说对吧?”
常氏叹道:“不瞒您说,以前我是有个执念的,但是最近竟然被人公然欺负,你说我气不气?现在我也想明白了,没个男人,就是没靠山,活该被欺负。”
“谁说不是呢?”
“老顾,不是我不愿嫁给魏二舍,只是怕他嫌我年纪大。”
“你今年多少岁了?”
“二十六。”
拐子笑道:“常言道,妻大二,米满贯;你俩真是绝配的,等我去给你说说看。”
“老顾,甭管好歹,记得来回复我一声。”
“当然。”
来到魏家,正碰见魏二回来,顾拐子拱手笑道:“二郎,你的喜事到了,我是特地来与你作媒的。”
“是谁家?”
“我不必说,想必大娘应该能猜得到。”
陶氏问说:“如果没猜错,那就应该是何阿婶了;我听说最近有人欺负他,所以她才要急着嫁人。”
魏二摸了摸脑袋,说道:“好是好,但咱家哪还有银子娶亲用?”
拐子说:“只要你答应,回头我跟她说说,少一点花红应该是没问题的。”
这边魏二没问题,那边常氏也乐意。看过了日历,两家急忙忙把亲事给办了。有些个熟人邻居来贺喜,免不了说些场面上的话。
等二人拜过了天地,常氏这才说起来:“既然我已经嫁到了你家,原来租的房子也没人住,不如就把它退了吧;家里的桌椅都是我置办的,还有些私蓄,你也一并搬过来。”
“有理,有理。”魏二点了点头,又说:“我明天就找人去搬。”
哪成想,常氏私蓄足有一百多两银子,喜的魏二合不拢嘴。自此之后,魏二竟从容起来,常氏接连给他生了两个儿子。陶氏婆婆还是照旧,每天吃斋念佛,只是把原来的菩萨尊身,换成了檀香的。陶氏得观世音庇佑,寿至九十六岁,无病而终。魏二得了妻子的私蓄,并在常氏的操持下,也逐渐做了一方财主。
由此可见:淫恶之报,如影随形;善人之举,自有佛佑。心存善念,一切随缘。
2022年女属鼠人的全年运势1984出生 2022年女属鼠人的全年运势如何 2022年女属鼠人的全年运势及运程 2034年进入辛卯大运时间 2034年进入辛卯大运的运势 辛卯大运 属虎水瓶座2022年运势分析图 属虎水瓶座2022年运势分析及运程 属虎水瓶座2022年运势分析 2023年白羊座婚姻运势详解女 2023年白羊座婚姻运势详解视频 2023年白羊座婚姻运势详解图 2021年12星座运势大解析 鸡年生人2022运程每月运势如何 鸡年生人2022运程每月运势详解 鸡年生人2022运程每月运势怎么样 白羊座2022年运势详解完整版半藏网 白羊座2022年运势及运程详解 属马人运势2023年每月运势 属马人运势2023年运势详解女 属马人运势2023年运势详解视频
copyright © 2022 一生命运网 版权所有 辽ICP备2022007116号-4
法律声明:本站文章来自网友投稿,不代表本站观点,版权归原创者所有,如果侵犯了你的权益,请通知我们,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!
